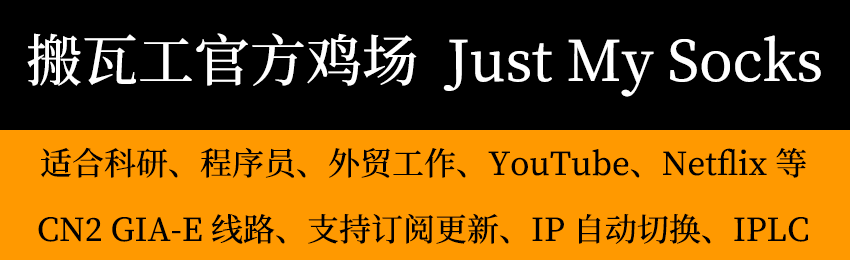
原标题:编辑,当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新世纪初的一天,《收获》主编程永新在北京三里屯的酒吧里和出版人丁
原标题:编辑,当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新世纪初的一天,《收获》主编程永新在北京三里屯的酒吧里和出版人丁小禾一起坐着喝扎啤,丁小禾对他说,“文学最好的时代过去了。你在文坛厮混了几十年,应当将那么多具有现场感的东西整理出来。”
回到上海之后,程永新给余华打了电话,问他那儿是不是还保存着自己的信,结果被余华浇了一头冷水,“谁像你几十年都待在一个办公室里,我已经搬了三次家,很难保存信件的。”
"
《一个人的文学史》
" "
作者:程永新
" "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
"
这是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的成书经历。2007年,这本书出了第一版,内容主要汇集了几十年间作家们的书信、程永新与作家们的访谈以及他的评论文字。2018年6月,重新修订后的版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换了三分之一的内容,增加了篇幅,上册主要是作家朋友们的书信,下册主要是他的评论文字,为增强现场感和生动性,他还把网络上与作家的交流内容收了进来,例如微博。《收获》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作用无可估量,作为重要编辑,程永新这本书就是30多年来中国文学现场的真实记录。
1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个人的文学史》研讨会上,程永新谈到当时他把锁在箱子里的那些信件找出来读的过程中,看到当年那些年轻作家的音容笑貌,他一边看一边笑,笑着笑着就笑出了眼泪。从1983年进《收获》当编辑到今天,一晃30多年过去了。
"
为什么大部分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是不成功的
"
“《一个人的文学史》给我们学院文学史写作的叙事提供了一个挑战”,这是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的观点。程永新这本书给像他这样写文学史和教文学史的人带来震动,文学史的书写一直强调更新已有文学史的观念,但往往忘记了那些活生生的历史。陈晓明感慨道:我们从来没有在活生生的历史现场中,去感受文学史,重写文学史。
同时,“一个人的文学史”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史的立场和态度。“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分成两种,一种要么是观念的文学史,要么是集体的文学史,我们都不敢说一个人的文学史。比如说当代文学史有上百部,可能有90多部是集体的,就几部是个人,是很少的。”陈晓明说。
程永新在发言中谈到,他读到翻箱倒柜找出来的那些与作家的通信时,又笑又流泪。在陈晓明看来,“含泪的笑”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史书写,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态度。
程永新的书中收录了非常多和作家间的通信,这些通信让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更近距离地看到作家。陈晓明开玩笑说,那个时候的嘴脸和今天的“道貌岸然”有一些出入,但是非常可爱,谁没有穷迫的时候?“我们今天就穿着汗衫,穿着三角裤亮亮相,秀秀肌肉,可以说是给文学史秀肌肉的一次写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 "
王朔的来信
"
而在作家阎连科看来,所有的文学史归根结底都是个人的文学史,不存在公共的文学史,即便是官方书写的文学史,也是代表某一个人的意志的。
阎连科认为,文学史的失败都在于文学史一定要公众化,如果文学史彻底放下公众化,文学会非常发达,而今天的文学史恰恰特别统一化。“文学史就应该是个人的文学史,不应该是某个文件政策的文学史。”
苏州大学教授王尧则顺着上述思路,提到“文学史的民主化”这一问题。多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教科书式的文学史,这种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成为最主要的知识生产方式,但王尧坦言,大部分教科书文学史都是不成功的,而且贻害无穷,他认为看教科书的文学史是不能成为学者的。
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王尧看来,它只是以文学史家、批评家、教授的身份,非常专断地取舍、发言,在这个过程中把编辑家、文学活动家、组织者和批评家在整个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疏忽了。一部好的文学史,应该有很好的注释,能够看到文学批评的学术史隐秘,而不是简单地独断专行地下一个结论,而把许多其他方面全部省略。在这个意义上,程永新的《一个人的文学史》突出了文学史写作的民主化的问题,打破了过去那种特别体制化的教科书文学史的写作。
评论家李敬泽自己做过28年文学编辑,他说28年的编辑生涯中,他的一个重要坐标就是程永新。李敬泽也认为,一个人的文学史这个观念是特别值得探讨的,今天的文学史特别需要这样的逻辑。新时期文学虽然才40年,但已经形成了诸多根深蒂固的定见。李敬泽讲到他看到的一个新时期四十年文学史展览的解说词,直接抄了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等条条框框。
“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当代文学学了半天就是学了这么几大块,就是这么几个框,就开始往里面装。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装不进去的。如果仅仅这几个框也乏味,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李敬泽说,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文学史》应该成为当代文学史教学的必备参考书。
"
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生态:编辑掌握一个作家的命运
"
文学评论家白烨谈到,最近举办的那么多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文学纪念活动里,文学编辑起到的作用是被忽略的。在《一个人的文学史》里,程永新写到许多名家名篇的修改过程。比如王朔的名篇《顽主》就有一段改名的故事。王朔曾在1987年9月的一封书信中回复程永新给小说《五花肉》更名的提议,“这篇小说我想会使正人君子有不好的感觉,所以名字尽可能鄙一些……”他还给出了几个书名选项:《毛毛虫》《顽主》《小人》《三“T”公司》。王朔更偏爱《五花肉》,“我当初取《五花肉》之名,借其既不全肥也不全瘦,红白全有,爆炒不行,小火炖烂了也挺香之意……”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文学史》讲了很多文学生产的内幕,是在别的书里看不到的。
"
九十年代格非与程永新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园
"
在场嘉宾中,作家苏童和程永新的交情很特别,他人生中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青石与河流》就是程永新发出来的。那是1986年,苏童才23岁,是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不知天高地厚的他给全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收获》投稿,结果被程永新看中了。小说发表后,苏童给程永新写了一封感谢信。“我又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外表平和俊秀,但是内心非常古怪的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大概要强调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我要引起他的注意。看这样的信真的是像闻自己的袜子。”
程永新也是作家李洱的伯乐。李洱记得,他第一次见到程永新是和格非一起。当时格非的稿子刚被《上海文学》退稿。那时的程永新也还不到30岁,简单聊了几句话放下稿子就走了,这让格非非常紧张,因为在那个年代,能在《收获》发小说意味着一举成名。忐忑不安的格非当时很愁,不知道要不要给程永新打电话,问关于稿子的问题。有一天终于打了电话,程永新告诉他稿子已经发了,就是让格非一夜成名的《迷舟》。
李洱还讲了一段轶事。当时张艺谋带着《红高粱》请上海专家看的时候,在北京火车站买了一本书,在火车上看完之后到上海就要找格非,拍《迷舟》,很快圈里面就传开了,随着《红高粱》的成名,格非也跟着成名了。
在李洱的印象中,当时的作家和编辑的交往跟现在不一样,因为当时的编辑确实掌握着作家的命运。李洱还记得,当年他在华东师大宿舍里改自己后来的成名作《导师死了》,程永新把稿子退给他的时候,给了很多修改意见,比如特别让他注意讲故事的节奏。在李洱记忆中,再牛的作家给《收获》投稿时都像是处女作,因为有严格的要求,会有程永新这样的编辑给你反复修改。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
研讨会现场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通过阅读《一个人的文学史》,通过程永新和作家间的通信,看到了作家成名、文学潮流成型前的史前史。比如书中有两封信,一封是洪峰写给程永新的,洪峰说每次给你写信我都很沮丧,你一直在给我泼冷水,这就是作家的史前史。还有一封是著名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给程永新的,写的是“我一篇稿子被上面退了,你方便的时候能不能帮我取回”,我们通常看到的都是成功的作家的信,没有看到作家成功之前的信,这就是史前史。程光炜谈到,今天做80年代先锋文学研究的时候,特别缺乏程永新手头那些第一手材料。
李敬泽也谈到,如果围绕程永新做博士论文,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题,像程永新这样的老编辑就是一个宝藏,现在仅仅拿出了几样东西,还没有真正打开。李敬泽鼓励当代文学研究界给程永新鼓劲,打开自己的宝藏。
作者:沈河西
编辑:董牧孜;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