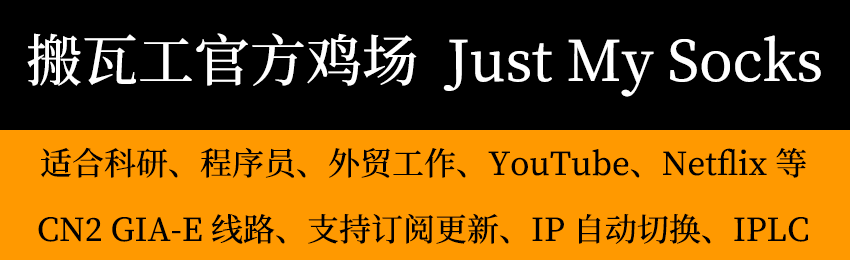
我在上海住过小十年。
那时小区附近便利店,是罗森、全家、良友金伴三足鼎立。
那时全家的便当好,罗森的货色齐,但我还是爱去良友。
除了因为那家良友的夜半关东煮,很适合那时还习惯熬夜的我,还因为良友那位阿姨。
我刚从学校搬出来住时,离我最近的地铁站是中山公园站;后来娄山关路地铁站起来了。
天山到虹桥之间,拆了个电影院,建起了几栋商厦,许多店在改头换面。我比较宅,对街上一举一动不太熟,但阿姨什么都懂。
“隔壁的粥弗要吃,不好吃。”
“弗要去菜场买西瓜,街对面西瓜摊头过两天就要开了,南汇过来格。”
“茶叶店新茶叶蛮好。”
“个边百味鸡弗要买他们家的鸡,要买他家的夫妻肺片吃。”
“小区门口那家鸡店(我们那里开了许多家某鼎鸡)弗好吃了,你要吃鸡,去地铁站那里吃……”
那还是个可以三位数一个月租个单间,到我离开上海时月租才刚涨到四位数的时代。我也知道早晚会离开上海,所以没太上心。
但从我入住,到2012年我离开,她一直孜孜不倦劝我:
“要买房子呀,还是房子牢靠,真格,有钞票就买房子。”
现在想起来,对我这样花碎钱买点日用品的,还这么实心实意的阿姨,我能遇到,真也是我的幸运。
对我而言,她就是最具体的上海人。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那时登了我稿子的杂志和报纸,偶尔会给我寄样刊,我邮箱里拿了,堆在书架上。
——只有一次,是我自己去拿的:2008年NBA总决赛第四场前,我骑车一直到我写稿的某个杂志社去见编辑,聊天,大家一起看了总决赛第四场,即凯尔特人24分逆转之战;然后我当场借了编辑部一台电脑写了赛后笔记,然后骑车回家,顺便把杂志放在车上带回来。
2008年初夏时节,穿短袖在上海的树影下骑车,回去路上外带一份白斩鸡,还算挺惬意。
跑题了。
当时来收房租的一般是房东阿姨。有一次房东大叔来收钱,等我拿钱时,他自己看杂志,看得津津有味。我顺水推舟,说这些刊物,您都拿回去看好了。他很高兴,拿了一大捧回家,免了我50元房租。
之后,每个月换成他来收房租了。
后来有一次,他来收房租时,带了个亲戚和她的孩子来。因为我那时偶尔上某频道当解说,那孩子可能在电视上瞟到过一眼,于是赶来看热闹。亲戚指着我,对孩子说,“好好学习,将来就能像哥哥一样上电视了,晓得伐?”
那天房东觉得我很给他面子,于是免了我当月100元房租。
以前写到过,我在上海倒数第二个冬天了吧,冬夜回家,看到路边一位老先生在卖棉花糖。我,一半馋糖了,一半因为上海冬夜的阴湿,难受得想象力丰富起来,生恻隐之心,于是问那位老先生:
“您还有多少糖?给我做个大的!”
——想着这样一来,他就能收摊回去了。
之后的情况超乎我想象。
他老人家谢了我,一面真做了一个巨大的棉花糖,大到我得用举火炬的姿势举着——低手怕掉了,平端贴脸,平举胳膊太累了,只好举着。
这么大的棉花糖,当然没法在冬夜路上吃——我总觉得吃一口,脸都要陷进去。
那只好拿回家了。
话说,这玩意大到什么程度呢?那会儿我街区的通宵便利店,到了晚间,两扇门只开一扇,当然还能容一人走进去,然而这宽度,棉花糖就进不去了。
只好去门脸朝街的水果店,买点水果,兼带着一点花生(我们那里,水果店还卖点小零食)。在店里挑水果时,自然也只能单手举着棉花糖。店里另两位顾客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店主小伙子在收银台后面圆睁双目,柜台边一个姑娘看着吃吃地笑。
我挑好一只柚子去结账时,店主一边算账,一边时不时抬头看看我手里的棉花糖。我掏钱不易,右手举着棉花糖,左手掏兜拿钱包费劲,姑娘就把棉花糖接过去了,我谢了一声,掏钱;姑娘跟店主咬耳朵嘀咕了几句。
店主跟我搭话:
“这个拿着,不太方便吧?”
“是,我也没想到会做这么大。”
“吃得下吗?挺黏的吧?”
“估计吃不下,估计得吃一半扔掉。”
“我女朋友很喜欢这个,要不,你把这个给我,水果不要钱了。”
“行,谢谢了。”
于是店主接过棉花糖给女朋友,“你等我下班,辛苦了。”
我终于轻松了,拿了柚子回家。
转天去街角吃麻辣烫时,麻辣烫店的老赵还跟我说:前几天晚上,哦哟喂水果店的那一对拿了个大得不得了的棉花糖,吃一口麻辣烫,就一口棉花糖,哦哟喂搞得大家都看他们两个……
我也写到过,夏天,在上海,出门吃午饭回来,在一垃圾车旁,见对情侣站着,问怎么,答听见里面有小奶猫叫,大概怎么掉进去了。
后来想了想,垃圾车沿跟路边围栏等高,可能小猫在路边围栏淘气,失足滑下去了。
垃圾车里主要是碎树枝树叶和饮料纸壳,略深,我朝里面伸了半天胳膊,够不到;大家围着,正发呆,膀阔腰圆腰大十围的扫垃圾阿姨吃完凉皮回来了,问什么事;我们具以答之。阿姨便相了一相,擎起车子,把垃圾车轰的一翻,倾在地上,从树枝堆里拣出小奶猫。
然后开始重新扫。
我也记得在我家隔壁的送水工,记得平时喂小区流浪猫、爱打羽毛球、有点少白头的小哥,记得游戏机店的小哥和他和善的母亲,记得给我修棕棚的老爷爷。
记得西装衬衫打得端正、发际线不太高,爱跟我聊毫茶的茶叶店老板。
记得我在小区旁某中学门口,想救助受伤野猫被咬了一口后,帮忙打电话叫救护宠物的,顺便给我地址让我赶紧去打针的打印店老板。
我也认识爱在朱家角喝酒吃虾的上海人,也认识不去卢湾体育馆喊刘炜我爱你就不舒服的上海人。
许多人说起上海,会想起各色高大上的词汇。
我比较土,只能想起天山虹桥那一带的普通民居。以至于后来每次到上海,都还要住在中山公园附近。
看到互联网上说到一些很标签的上海人时,我总能想起冬日早上摸黑买生煎时,那些顶着星光往菜市场里运菜的普通上海人。我午夜去买关东煮时,对我谆谆教诲的上海阿姨们。
大概因为我认识的上海人还太少吧,肯定不够典型。
反正大多数我认识的上海人,如果不带着“他是上海人”的目光去审视,就觉得,都还是最普通的普通人。
就像我认识的沈阳的、营口的、铁岭的和长春的朋友,并不会对我“你瞅啥”。
当然不是说他们全无特征。至少十年前我认识的那些上海人,普遍推崇“拎得清”。
我合作过的编辑不算少。公私方面分得最清的,社交成本最低、不用多废话的三位编辑中,有两位是上海的。
当然,大家都是普通人,过普通生活罢了。
互联网时代,大家总是习惯选取最出格的行为,为一个地方画像。
比如你对一个没去过希腊的人说,“希腊人很爱吃烤肉”,大概会收获“这有啥?到处都吃。”
但如果加上“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那里人会吃山羊奶酪配蜂蜜”,大家觉得“好怪啊,不过听着很希腊!”
画像之后,就会形成对一个地方的基本认知,继而会对号入座,继而慢慢地:
“你居然不这样?你们那里不是都这样的吗?”
纳博科夫以前吐槽过,所谓文学流派细致划分,都是方便归类,方便教学用的。
他这话不免失之偏激,但我个人觉得有些道理。
大多数标签,都是为了宣传地方,自己急速描绘所就,以求印象鲜明。
以至于有些典型得夸张了——这也不奇怪,就像许多漫画像,为了方便人一望而知,总是会突出特征——也许是为了旅游业,也许是为了卖文宣。
毕竟老老实实告诉别人,“我们这里商业区就是一大堆全国都差不多的连锁快餐”,很难吸引人来吧?
但稍微走过多一点地方,认识的人杂一些,自然会发现:
不同地方,最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并不那么大。
这篇当然没啥时效性,毕竟我离开上海也快十年。
如今的上海与当初,肯定也大不相同。
只无非是些最简单的、大家想必都有体验的道理——尤其被人说过“你是xx来的?你不像那里来的人哦”之后,大概感受得格外明显?
大多数地域被塑造的典型形象,与其中实际生活的普通人,并不太一样。
许多差别度是人为夸张的,还有人喜欢迎合这种差别度,获得自我认同,或是让他的那部分受众找归属感——比如某位我吐槽过不止一次的、将咖啡与大蒜截然划分的先生——对他的论调,我还是那句话:对地中海沿岸许多地区,咖啡和大蒜都是生活必需品,甚至大蒜还重要过咖啡呢……
但我认识的。最普通的上海人,似乎没那么矫情——当然也可能因为我结识的多是街头巷尾贩夫走卒,不够高大上吧。
大概,显摆的人家处处与众不同,成为地区典型。
普通人家,到处都差不多。
又不只是上海如此。
不同地区, 最普通最广大的人群,都是忙忙碌碌,希望一日三餐生活平安,如果有闲暇有余裕,就稍微体面一点;你对其客气便能得到一点热情反馈——因为大家都不容易。
就是这些最大多数、最普通的大众,一个地方好了,出了各种都市传奇段子被说得神乎其神了,最享福最出风头作为典型代表的,往往不是他们。
但遇到变故,最先吃苦的,却往往是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