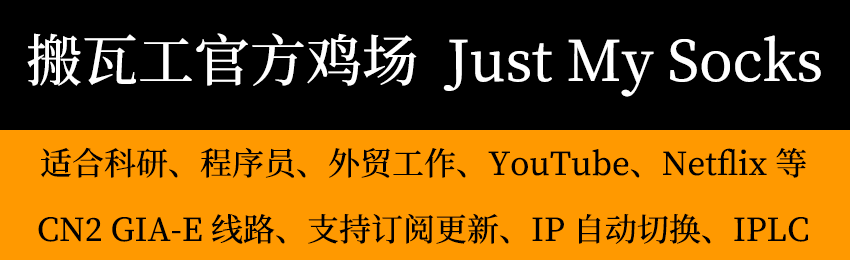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吴飞
张祥龙(1949.8.14-2022.6.8)
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先生于2022年6月8日去世。
《上海书评》刊发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老师为张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中西印哲学导论》撰写的书评,纪念张先生。
今年5月28日,北大出版社的王立刚编辑送给我张祥龙老师的新书《中西印哲学导论》(以下简称《哲学导论》),很自豪地说,这是他编过的祥龙老师第四本书了。翻开这本厚厚的著作,其中很多内容都是似曾相识的,从2002年开始,祥龙老师在北大开讲全校通选课“哲学概论”(2005年纳入哲学系必修课,改称“哲学导论”),就已经形成了此书的基本架构和思想,后来又在山东大学和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反复讲授和修改,历经二十年,终于出版了这部讲义。朱刚教授说,这应该是祥龙老师对哲学的最终理解。
《中西印哲学导论》,张祥龙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568页,128.00元
“哲学导论”和“宗教学导论”,是北大哲学系给大一本科生开设的入门课程,“哲学导论”曾先后请张世英、叶秀山、张祥龙、赵敦华、李猛等名师讲授。这门课很不好上,非常考验讲授者的见识和功力,既要对主要哲学流派和哲学家有非常专业的理解,又不能讲成哲学史(因为另外有哲学史课程);讲授者要有哲学性的思考,但又不能向学生灌输某一派哲学思想,而要能够展现出哲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作为学生进入哲学学习的门径与津梁,作为接引大一学生从高中转入大学学习的课程,还要深入浅出,帮助学生成功地完成过渡,而不能将学生吓跑。总之,“哲学导论”这门课,是最应该由有哲学家气质的老师讲授的课程。我2005年回到哲学系任教的时候,正是祥龙老师在上这门课,2006年,我开始讲授“宗教学导论”,与祥龙老师搭档数年,深知祥龙老师对学生的吸引力。很多学生是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哲学的魅力,开始走上哲学之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祥龙老师成为北大哲学系的象征:他的飘飘长髯、整洁的唐装、洪亮的声音、高远的气象、严谨的学风、风趣的语言、精光四射的双目、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以及跨越中西印三大哲学体系的讲义,处处都呈现出一丝不苟的哲学家的赤子之心。
很羡慕我的那些学生,能够接受如此精醇的哲学教育。这对于我自己的课,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鞭策。但我当时也回想起,在十年前,也就是我还在哲学系读硕士的时候,也曾经听过祥龙老师的几门课,感受过他的哲学魅力。当时祥龙老师也是回国没有几年,四十多岁,刚刚出版其成名作《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那时的祥龙老师,深深的眼窝上架着一副眼镜,喜欢穿西装和夹克,文质彬彬,非常帅气,不仅显得非常年轻,而且很洋气——得知他出生在香港后,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很难想象他和靳希平、赵敦华老师都是1949年生人。据说有一次他们三人一起坐公交车,祥龙老师有座位,靳老师和赵老师都站在旁边,售票员说:“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座位不知让给老人坐?”我在他的课上也听到了中、西、印三大哲学体系,也听了他讲海德格尔。上他课的时候,我正在准备申请去美国读博士,非常冒昧地去请祥龙老师写推荐信,当时很多中国老师乐得做个人情,往往就答应了,甚至会让学生自己写,然后签名,但祥龙老师却以对我不够了解为由婉拒了。这次挫败使我深刻体会到了祥龙老师的严谨方正。
左起:朱东华、Melville Stewart、张祥龙,吴飞,刘凤罡,摄于1996年秋。
等我回到北大教书,祥龙老师已经与十年前大不相同了。他不知何时蓄起了长长的胡须,再也不会被人误认为小伙子了,更重要的是,无论他的学问还是授课风格,都已变得更加圆融老到,但其哲学的活力和其中深深蕴藏的赤子之心,却呈现出更加蓬勃的朝气。作为同事和搭档,我开始更近距离地接触课堂之下的祥龙老师,体会到了他的温和与热情,可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随着祥龙老师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清晰丰满,我也对他的哲学思考有了更多的了解,但直到读了这本书,才对他的思想有了比较全面的把握。这本《哲学导论》,可以算作他哲学思考的总体架构,也是了解他哲学思想的最好入门书。
此书以哲学问题为线索,从中国、西方、印度三大哲学体系比较论述,分为七大部分二十一章,第一部分总述哲学的含义与东西方哲学家,第二部分是终极实在,第三部分是知识论,第四部分是伦理学,第五部分是政治哲学,第六部分是美学,第七部分是当代西方哲学。
边缘问题
在全书的序言中,他给出了自己对哲学的独特理解:“哲学是对边缘问题的各种合理探讨,与流行的‘世界观’‘方法论’‘总规律’‘科学的科学’‘批判理性’‘澄清语言的逻辑结构’等说法都不同。”这真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哲学定义,他随后做了澄清:“‘边缘’意味着半实半虚的境地,超出了现成的理性手段,要面对深邃的不可测,但毕竟还是站在广义理性之中,要讲出一番道理,可加深我们对自己生存和所面对世界的理解,而不只是激发感觉和形成信念。所以哲学不是科学,当然也不是科学的科学,而科学在其边缘处或大变革时,倒可能是哲学。”(《中西印哲学导论》,第1页)
祥龙老师说的“边缘”,并不是通常理解的“非中心”的意思,而是既受到其现象学思考的深刻影响,又带着佛教禅宗的味道。在他的哲学思考中,祥龙老师对“缘”这个字情有独钟,他将现象学的Horizont一词译为“构成边缘域”或“构成境遇”:“一切意向性的体验中都有一个围绕在显示点周围的边缘域,它总已在暗中匿名地、非主题地准备好了下一步的显示可能性。”(《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5页)更重要的是,他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核心概念Dasein译为“缘在”,将Da译为“缘”,并如此解说自己的译法:
这个Da具有相互牵引、揭示开启、自身的当场构成、以自身的生存活动本身为目的、生存的空间和境遇、与世间不可分、有限的却充满了发生的契机等意义。考虑到这些因素,中文里的“缘”字可以用来比较贴切地翻译它。这不仅是因为“缘”字基本上具备了这些含义,而且由于历史上的佛经翻译使用了这个词,使它那些含义在一千多年的中印文化交融的语境中被酿出了更加丰富微妙的思想含义。而且,龙树的《中论》消除了佛家“缘起”说中的种种杂质,比如因果缘起说、聚散缘起说,给予了这“缘”以无任何现成前提的或“空”(sūnyatā)的存在论含义。(同前,94页)
《海德格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张祥龙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9月初版,459页,22.80元
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Dasein的含义与译名》,更详细深入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对以“缘在”翻译Dasein,给出了六个理由:第一,《说文解字》以“衣纯”释“缘”,本有边缘、束丝之义;第二,由此引申出“攀援”“凭借”之义;第三,攀援、凭借既包含了“因由”,又有“机会”之义,因而有原本的“时间”含义;第四,边缘有“有限”义;第五,边缘衍生出“围绕”“沿着”之义,皆与“空间”有关;第六,最重要的是,佛教已经用“缘”来阐释“缘起性空”这样的中心思想(《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年,84-86页)。
他在描述《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之主旨时说:“这本书中对于海德格尔、中国天道观(儒、道、兵、法等)及其关系的讨论中都有这样一个境域构成的张力背景。没有这种被现象学者称之为边缘域或构成视野(Horizont)的领会晕圈,关于人文现象的比较研究就会或牵强或不及,而达不到相摩相荡、氤氲化醇、‘其言曲而中’的对话境界。”(《海德格思想与中国天道》,第1页)此书的副标题是“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他在脚注中说:“本书中‘视野’‘视域’‘境域’‘境界’‘缘境’‘境’是一组同义词。只是,有‘视’的词突出人的纯体验的一面;而有‘境’的词则更多地意味着这体验的源泉和归宿。不过,很明白,这‘视’和‘境’水乳交融,相互做成。没有哪个视野中能无境,也没有哪个境界不在视野的构成之中。”(同前,16页脚注)在正文中,他提醒读者,这里的“源”字亦可作“缘” (同前,13页)。正是视野与境界水乳交融、相互做成而相摩相荡、氤氲化醇的体验,构成了祥龙老师哲学思考的缘在。
《现象学导论七讲:从原著阐发原意》,张祥龙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修订新版(2003年1月初版),381页,48.00元
对于海德格尔使用频繁的Ereignis,他则译为“缘构发生”,并解释说:“海德格尔要用这个词表达这样一个思想:任何‘自身’或存在者的存在性从根本上都不是现成的,而只能在一种相互牵引、来回交荡的缘构态中被发生出来。所以,这个词可以被译为‘自身的缘构成’,或含糊一些地译为‘缘构发生’、‘缘发生’。” (同前,163页)
这几个本来在字面上没有直接关联的概念,被祥龙老师用“缘”字牵连起来,这种牵连方式,已经展现出其独特的哲学视角和世界文明观。他认为,仅有中西哲学的对话与比较还不够,为了使这种比较“更广阔、更具蕴育力”,还需要找到“位于中西之间的第三者或参照者,使得整个对比研究获得新的一维”,这一维就是印度哲学(同前,第4页)。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看重佛教汉译对“缘”字的使用。初看《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的目录,我很不理解为什么要有相当的篇幅谈印度哲学,但深入阅读祥龙老师对边缘域、缘在和缘构发生等概念的思考,就会清楚,印度哲学是其哲学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祥龙老师早年跟随贺麟先生读哲学,已经形成了中西哲学双向思考的格局,后来在美国跟随一位印度老师读硕士,这种难得的哲学缘使他能够在中西印三大哲学体系的相互激发之下展开思考。在中西印三大思想体系之间做哲学思考的,前有梁漱溟,后有丁耘,但祥龙老师和他们二位的用意都很不一样。他勾连三大体系靠的是“缘”,使三个哲学传统交叠构成了他的边缘域,这在祥龙老师哲学思考的开端就已经初具规模,那时候,读者往往还不大能理解,但在他后来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践行中逐渐展开,越来越成熟,最终呈现为《哲学导论》中的这一形态。
张祥龙与贺麟先生,摄于1980年。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对哲学的定义,也就能够理解,哲学所处理的“边缘”问题,并非远离中心的次要问题,而是呈现在这视野和境界之间的,极其重要,却不能被确定的科学话语所涵盖的问题:“它出现在面对‘不可测’的边缘形势中,当我们穷尽了现有的手段,比如技术化的、常规科学的、感官常识的、概念推衍的认知手段之后,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但是它又好像可以被解决,而且在深入的追求中,的确可能得到时机化的解决。”(《中西印哲学导论》,10页)他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个注定要以死亡结束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题,当然是常规科学所无法回答的,却正好落在他的终极视域中:“总之,‘边缘’意味着活的终极,它让思想走到了头儿,立于悬崖边上,因此它是半有半无、半虚半实,既不能作为对象、哪怕是观念对象被把捉到,却又牵涉全局,可以是那‘动全身’的‘一发’。”(同前,11页)他将边缘问题的主要特征称为“非定域性”,以量子力学来说明。这个“非定域性”,与其早期思想中的“视域”“境域”“构成域”等说法是何关系?他之所以强调“视野”和“境界”的水乳交融,是因为以科学确定性为特征的定域,是无法与视野交融的,两相交融的边缘域,是境域,却并非“定域”,像“人生的意义”“什么是幸福”“生死问题”“世界的开端”等问题,都具备这样的特点,却绝非不重要的问题,反而是最重要的问题。“总之,哲学就是要应对边缘问题,它永远出现在人类精神的惊涛骇浪处,不可能是四平八稳、一劳永逸的。如果你凭借一般印象而认为,哲学是一套体系,哲学家必须是那种通过构造概念化学说来告诉你世界是怎么回事、灌输给你一个世界观的论证,那就错了。”(同前,22页)
时间观
在上述对哲学问题的界定中,他特别强调“时机化的解决”,后文又说:“边缘问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有时间性和情境性的。”(同前,21页)对时间的理解当然也是祥龙老师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结果。在《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中,他非常详细地分析了海德格尔的时间学说,并以此触及了海德格尔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意识:对主体性的重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面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传统(吴增定:《〈艺术作品的起源〉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革命》,《文艺研究》2011年第九期),至于他们是否成功则有很大争议。萨特就批评海德格尔丧失了自我意识,而祥龙老师认为,萨特没有看到,海德格尔的缘在分析和先行决断“已经比前人的自我分析远为微妙地揭示了‘自我’(包括意识的自我)的那些有活力的存在论特征,同时滤掉了传统自我意识观中的‘内在的’、私有的、心理的和现成的东西”(《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133页)。在他看来,海德格尔从思想的角度已经达到了佛家禅宗既讲缘起,又讲自性的境界。海德格尔是否如此完美地解决了主体性问题,恐怕还有可商榷的余地,但这对祥龙老师自己的哲学思考,无疑是有深刻影响的。他说:“缘在在历尽人间幻境、死亡的熬炼、良知的发现和决断的开悟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身所在:时间性。”“缘在说到底就是这样一种纯缘构着的时间境域。”(同前,134页)坦率说,这种充满激情的语言方式与海德格尔那种极其冷峻绵密的语言方式颇有距离,但我们从中更多看到的是祥龙老师被海德格尔打开的汹涌哲思,看到了其边缘化哲学意识中充满时间性和情境性的生命律动。缘在对时间性的探询,更多像是祥龙老师的夫子自道。
《海德格尔传》,张祥龙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335页,18.60元,该书的题辞为“献给恩师贺麟先生”。
说祥龙老师很具哲学家气质,不仅在于他思想中的原创性,更在于他对终极问题的哲学思考,都深深植根于自己的人生阅历与体悟。祥龙老师和他的哥哥年轻时曾经积极参与红卫兵组织,到各地串联、扒火车,做过很多轰轰烈烈的事,而且还在一些同学的鼓动下办了一份报纸,写过影响很大的文章,他也因此遭到批判,自己曾投入极大热情的理想幻灭了,他一度陷入深刻的绝望、怀疑与苦闷中。由于母亲与贺麟先生夫人是同学,祥龙老师找到了尚未获得平反的贺麟先生,成为私淑弟子,读了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哲学家的著作,在这样的哲学阅读与思考中逐渐走出人生低谷。那个时候他找到的是否就是“时间性”已不可知,但“人间幻境”“死亡的熬炼”“良知的发现”“决断的开悟”,肯定是曾在他内心反复翻腾、屡经锻造的边缘体验,促使他去思考终极问题。他对中国思想中时机化的时间观的极具原创性的研究,正是他在反复体验人生况味之后的哲学提升。
青年时期的张祥龙
由于种种原因,在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传统中,时间问题很少被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中来。但从《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开始,祥龙老师就非常关注这个方面,这也成为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关于这方面的初步思考,请见拙文《身心一体观与性命论主体的确立》,《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六期)。祥龙老师在对中国古代各大哲学家天道观的研究中,非常关注时间问题,并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中最本源的时间思想并不在五行或五德循环的说法之中,而是在天道的时机化之中。”所谓时机化,是对海德格尔Zeitigung这一概念的翻译,“主要是指人的不同种类的生存方式,比如‘处身情境’‘领会’‘与人们共在’,实现自身的时间模式,即以时间三相中的哪一相为首要的逸出态(Ekstasis)而构成自身”(《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374页)。由于海德格尔时间观深刻地转化了西方时间历史观,从而“既深入了时间境域的思路,又没有失落掉理性的终极追求”(同前,371页),“海德格尔的时间观与天道时间观有着关键的相通之处”,“它们都既不是物质自然的时间观,也不是目的论的时间观,而是缘发境域的自然时间观”(同前,373页)。天道本身既有时间性,又是时机化的,“‘时中’而非‘对于永恒不变者的把握’是最高智慧,这一见地不会产生于西方和印度的主流传统,而只能出现于天道文化中”(同前,373-374页)。但也是在时间观和时机化的问题上,祥龙老师深刻意识到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天道思想的相异之处。他无法接受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时间指向,认为“用时间的时机化方式来重新解释缘在的存在形态的路子缺少真实的思想开启力”。“海德格尔的时间观和后期的语言观,除了开出一个新的思想天地这一伟绩之外,似乎对我们的人生并无直接的帮助。”(同前,374-375页)另一方面,他对于充满时机化的中国天道观同样不满意:“中国天道思想家们长于境域中的机变和洞察,却疏于反省其根据,并说清未何只能如此的道理。结果就是,这时机化的终极观不能再被后来的玄学家、理学家、心学家们所领会,只能在各种被士大夫们视为雕虫小技的技艺中东露一麟、西伸一爪了。”(同前,376页)与他充满热情讨论的其他问题不同,他对时间,特别是时机化的思考中有很多保留和意犹未尽的地方,而这也恰恰为他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思考与提升的空间。
1992年春,张祥龙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海德格尔与道家》。
天之时与天时
2016年深秋,我和祥龙老师一同乘车去八宝山,参加叶秀山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一路上,我们聊了很多话题,他特别谈到自己遭遇《周易》的经历,说是易学为他打开了理解中国时间观的钥匙,而当时我也开始接触易学,苦于找不到门径,他告诉我,自己是通过读潘雨廷先生的书进入易学的。我听了他的话,迅速下单买到了潘先生的书,果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在这个方面,真要特别感谢祥龙老师,而我也由此看清楚了他时间哲学转变的关键,是1999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时观》一文。
文中首次详细讨论了《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中未能深入处理的《易》学和五行循环,区分了“天之时”与“天时”:“我们可以称‘时制’‘四时’等意义上的天时为‘天之时’,即天的时间表现,而称原本微妙的天时为‘原发天时’或‘原发时间’。”(《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二期,62页;亦可见《从现象学到孔夫子》,204-228页)这对区分非常类似于宋代易学对后天八卦与先天八卦的区分。易学与五行相结合,以模拟四时历法变化,应当是易学时间观较朴素的形态,按照震、巽、离、坤、兑、乾、坎、艮的次序构成的八卦方位图,与木、火、土、金、水之五行次序相应,代表了东、南、西、北之方位和春、夏、秋、冬之四时。祥龙老师又提及的十二辟卦、卦气七十二候、六日七分诸图,都是结合易象与历法来看待时间的,即“天之时”。董仲舒之《春秋繁露》,正是以对天之时的阐释,形成了一个虽不免呆板,但非常系统的思想体系,祥龙老师将董氏之说理解为,“从阴阳五行的气化变易学说衍生出来的理性信念,也就是将原发时间观以比较呆板的方式运用到人生的具体情境中来的结果”(同前,70页)。而“原发时间或‘易时’绝非线性的,也不是形式上循环的,而是氤氲醇化而生的时境、时气。更重要的是,这‘相推而生’的原发时间必与人的‘彰往察来、微显阐幽’之‘知’不可分。也就是说,此原发时间乃是‘时机’,得此时者必‘知几’,而能以‘神’会事”(同前,62-63页)。《系辞》云:“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牟宗三先生已然注意到“几”在《周易》哲学中的关键作用(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11页),却并未从时间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祥龙老师则指出,知几就是知时机,乃是易学时间观中的时机化。其实,知几的朴素含义仍需要在天之时的维度上来理解。一叶落而天下知秋,便是历象天文的知几。但易象卦爻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阴阳和合而成的各种时机(或“几”),体现的是一种更加灵动的时间观,远远不止是一个更精微的“天气预报”,而是对人生处境中各种吉凶悔吝之事的时机感。在我看来,这正是宋儒画出的先天八卦图,即按照阴阳次序排列的,自南向西向北向东为:乾、巽、坎、艮、坤、震、离、兑。由于先天八卦规律更明显,汉易中的方位图就被称为后天八卦。同样,祥龙老师认为天时是更原发的时间观,而天之时是更呆板的时间观,但天时是建立在天之时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对天之时的历法时间更深入的解释和更巧妙的运用。
《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张祥龙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4月出版,407页,22.00元
祥龙老师所区分的天时与天之时,乃是中国时间观中的要害。他很强调天时对天之时的超越,但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抽象地从时机化来讲“见机而作”和“圣之时”,则有可能会流入凡俗的投机之弊。时机化的“知几”虽不必固着于春夏秋冬的固定循环模式,却总会追溯到生长收藏的性命节律,阴阳交合亦终究来自阴阳消息的天之时。只有坚持从性命节律出发,辩证地看待天之时与天时的关系,才能使之成为对根本性命处境的一种关照。也正是因为对这一点越来越清晰的认识,祥龙老师的时机化研究始终拒斥申韩权谋之趋向,而是走入对慈孝意识的研究。他在2006年刊发的《孝意识的时间分析》中,不再仅以外在的伦理观来看待慈孝之德,而是指出:“‘孝爱本源论’之所以能在古代中国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易》阴阳时间观的存在,不仅《易》的爻象与卦象有父母子女的含义,而且《易》中的‘时义’之深邃宏大和生存化,也会促进人们对于慈孝现象的哲理理解。”(《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一期,24页)这一思想后来在《舜孝的艰难性与时间性》(删节版载《文史哲》2014年第二期,全文收入拙编《神圣的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和《孝道时间性与人类学》(《中州学刊》2014年第五期,后收入《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等论文中又有一进步的阐发,且体现在其《孔夫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商务印书馆,2019年)一书中。《“美在其中”的时-间性——〈尧典〉和〈周易〉中的哲理之“观”及与他者哲学的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二期)一文,则是更全面阐发其中国时间哲学的力作。文中将《周易》“观”卦“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尧典》中的观象授时,以及舜孝之时间性及其事业的时慧大美关联起来讨论,在天之时与天时、天时与人时之间,搭建了一个更为宏阔与圆融的时间哲学和美学。
张祥龙儒家哲学史讲演录:《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2009)、《从〈春秋〉到荀子》(2009)、《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2012)、《儒家心学及其意识依据》(2019)
天鹅之歌
《哲学导论》为祥龙老师留给哲学界的最后告白,呈现出这一系列思考的最终形态,不仅是以时机化和情境化来理解边缘问题,更是将其贯穿在全书三大体系最根本哲学问题的展开中。相对于希腊人为西方确立的、以追求不变为最根本特征的终极实在观,祥龙老师以《周易》中的易、阴阳和卦变时几为中心,阐释中国古代的终极实在观,指出:“易象既不是几何的图型、事物的形象,也不是一般的数字,也不是形而上学的静态结构,而是引发我们感受变化的能力的那种意象结构,所以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边缘问题。”因而,孔子“通过领会《周易》阴阳时几的要义来深究人生本身乃至国家、文明兴亡的趋向,从这个大占卜中得出了儒家对人生和世界的根本性理解。比如什么是美德,什么是仁政,什么是天道和性命等等”(《中西印哲学导论》,104页)。
正是由于终极实在是处在变易中的,因而在认识论上,主客之间的硬性对象化而导致的无公度性问题便很不突出,“认识的要害和神髓就是要知几”(同前,163页)。在伦理学上,相对于西方具有强烈普遍主义倾向的、抽象的、全知预设的善恶观,强调亲亲为本,通过学习六艺,达致时机化、中庸和并非对象化的乐感(同前,264-275页)。在政治哲学上,相对于西方基于二元论思维的权力、契约政治,特别是重内政、轻国际的特点,祥龙老师以四个断句概括西周到孔子的政治观:天道变化,天人感应,以德配天,文化多样(同前,321页)。讨论华夏诗乐境界之美学的部分,是《“美在其中”的时-间性》中基本观念的进一步阐发,认为美的根本来源在于几微之象,“易象是引发意义和存在的结构表现,因此也可称为‘[构]意[之]象’,充溢着时几、态势、丰饶(冗余)、回旋和晕圈(气象)”(同前,415页)。
以上是以其“边缘问题”和“时机化”为纲领,对《哲学导论》一书主要部分的极简概括。与其起步之时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相较,此书仍然包含了中西印三大体系的基本视野,仍然以印度哲学为媒介,旨在对比中西哲学,且其中的主要观念在早期著作中已见其几。但将其一头一尾两部书对比,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早期那本书,通过从海德格尔哲学中学到的哲学观念,来考察中国天道,并进而对比中西,同时展现出中西两大哲学体系的广阔与纵深。现在这本书,虽然每部分仍然是以西学开篇,但以作者已经相当成形的中国哲学视角来评判各大哲学体系,虽不乏对中国和印度哲学的揄扬,对西方哲学却并非批判,而是仍能充分展现出其精妙、伟大与丰富。三大哲学体系在面对边缘问题时相互激荡与对话,各自呈现出自己的魅力,是这本书一个重要特点。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早期那本书对中国天道的阐发是以老庄为主的,但经过近三十年的思考之后,这本书已经将孔子和易学作为理解中国哲学的主线,对老庄和其他相关各家虽亦尽可能展现出其丰富体系,却使之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因而形成一个以易学为主线的中国思想观。
2007年,五十八岁时的张祥龙。
《哲学导论》中相对薄弱的是政治哲学部分,而美学部分则尤其能彰显祥龙老师思想的灵动与气韵。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大哲学问题之后,他特别增加了最后一部分“当代西方哲学”,但其中并未专门谈他最擅长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而是讲了伯格森、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最后一章是“梭罗和中西哲学的当代共鸣”。这种意味深长的安排,和他研究海德格尔时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一致的:当代西方哲学越来越突破其传统的对象化视野,走向与中国哲学的共鸣,也为中国哲学回答当代世界的普遍问题创造了时机。以梭罗作为终章,不仅暗中呼应了前一部分美学,更重要的是,与祥龙老师自己的一段经历有关。
早就听祥龙老师大学时的同学说过,在他们即将毕业之时,祥龙老师神秘地失踪了,有人说他出家了,有人说他隐居起来了,有人说他去修道了,人们大多不知道详情。在《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的“后记”中,他说:“一段时间中,我感到绝望,很想到山中静居,直接体验那‘言不尽意’的道境。”(《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455页)在一次闲聊的时候,祥龙老师告诉我,他是在京北山区(是昌平、延庆还是哪里,已经记不清了)找了一个农家院落,住了进去,每天清晨起来登高望远、亲近自然、沉思天地,他因此还成为北京环境保护局的一员,“从事自然保护工作”。那个院落被他长期租下来或是买下来,在中国房地产业尚远未起步的时代,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一件事。但无论如何,那不是一个舒适宽阔的别墅,而是一个非常简陋狭小的房子。后来,祥龙老师隔一段时间就去那个院落去住一住,找回天地大美的感觉。我们在他的著作中不时能看到“于塞外蜗居”的字样,指的就是那里。对他而言,这里如同海德格尔的托特瑙山,如同梭罗的瓦尔登湖,是哲思栖居的地方。
吴飞和张祥龙在前者组织的“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家”研讨会,2013年6月23日。
在祥龙老师离开北大,相继赴山东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之后,我就不是经常能见到他了。但忘年相交,莫逆于心,一年半年遇到一次,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也总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我组织的几次学术会议,他都非常热情地参加,和年轻人在会场上非常认真投入地争论。2017年,我的《人伦的“解体”》书稿完成,交给三联书店前,他为我写了一封充满溢美之词的推荐信,我都不好意思交上去。——终于弥补了当初未能得到他的推荐信的遗憾。有一次,我和他一起乘机去广州,飞机晚点六七个小时,在首都机场,他向我大讲量子力学,这成为继易学之后的又一次知识启蒙,为我打开一个新的世界,以至于一会就被喇叭催促登机,都没觉得时间过去了。到了飞机上,他坐在我后面三四排。一路上我抱着一本书读得津津有味,心无旁骛,中间听到广播找医生,说一位乘客在呕吐,我也混未在意,直到落地之后,才发现就是祥龙老师,因为旅途颠簸而呕吐不止,此时他虽已止住,却也面色不好,这令我着实惭愧,而祥龙老师还一再说:“没有什么,已经好了。”
之后两年,得到了祥龙老师生病住院的消息。但2021年初,在北大医院体检的时候,我又遇到了祥龙老师,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张开双臂扭扭腰说:“你看,已经没任何问题了。”他的身体确实恢复了,还去美国带了一年孙子,刚刚回来,向我讲起美国疫情的状况,深以中国而自豪。
步入晚年的张祥龙
2022年的古典学年会,为了提振久已萎靡的人文学术界的士气,激发问题意识,我们设定了“海德格尔与古典”为年会主题,很多人觉得,这简直是为祥龙老师量身定做的。在2021年年底,我给祥龙老师发邮件,邀请他参会,在元旦那天,接到了他一封简短的回信:“吴飞兄,我最近体检出了问题,今天又有不利的信息。可见的将来不可能参加这样的活动了。非常抱歉!新年好!张祥龙。”原来他查出了胰腺癌,又在疫情期间,我很想去探望,却终究未能成行。据见到病中的祥龙老师的朋友们讲,他虽然承受着癌症带来的巨大疼痛,每天靠吃药止痛,非常憔悴虚弱,但长须依然不乱,神态依旧俨然,一身唐装仍很整齐,仍然在和朋友与弟子们讨论着哲学问题,而且从不讳言痛苦和死亡。在疼痛比较剧烈的时候,他会说:“我做不到像苏格拉底那样,但苏格拉底也没有受这样的身体折磨。”而今的他,正站在“悬崖边上”,经历“死亡的熬炼”,再没有比这更真切的边缘问题了。祥龙老师终于要面对“向死而生”的问题,那个曾让那么多人迷上海德格尔的命题,这位海德格尔专家却颇有保留。而今,他切切实实地告诉大家,他对这个命题的保留并非虚言。真真切切的痛苦和折磨没有使他放弃自己的坚持,他到最后时刻仍然在拒绝对象化,仍然靠自己的信仰期待着美好与真实。这个深知有生必有死的缘在,面对最终极的边缘问题,仍然在以其思想中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为的不是虚幻的价值,不是不变的静止存在,而是永远活泼泼的生命力量,依然可以感受到“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的生命之美。在这精神的惊涛骇浪中,他经常引用的这句诗应该最能描述他的状态:“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