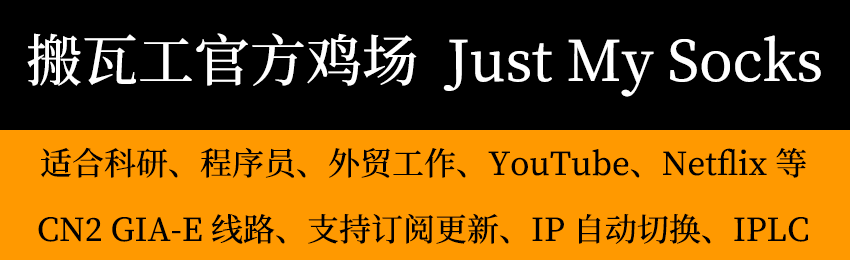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宗璞《紫藤萝瀑布》
还记得小学课本里这篇著名的散文《紫藤萝瀑布》吗?这篇文章写于40年前的1982年5月,彼时宗璞的弟弟身患重病,作者非常悲痛,徘徊于庭院之时看到一树盛开的紫藤萝花。她睹物释怀,感悟到生命的短暂与永恒。
盛放的紫藤花,图片/IC photo
实际上,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艺术史上,有诸多对于紫藤花的描绘。但不知为何,紫藤花一直不像玫瑰、荷花或者梅花、菊花等有着鲜明的烙印,它总是处于被忽视的边缘。但这不影响紫藤花每年春夏时节的盛放。初夏时节,正值紫藤花的花期,随着夏日到来,紫藤花也很快会落尽散去。
如同《紫藤萝瀑布》中所写,对于花朵的欣赏总是提醒着我们珍视短暂而永恒的生命:“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沉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在这篇长文中,作者细细考证了紫藤花在植物学、文学乃至绘画史上的趣闻轶事。阅读这些关于紫藤花的词文,也唤起我们对自然与生命的爱意。
说来可笑,虽然很早从文学作品中接触到了紫藤,但紫藤其物,我是直到读研究生了才真正认识。读研时的一个春日,与先生在校园里散步,远远望见一处花架紫云垂地,先生问,“紫藤花你吃过吗?”正沉浸在梦幻般带着淡淡香气的紫烟中的我,猛然回过神来,原来这片紫烟就是宗璞笔下的紫藤呀!忽想起古龙笔下那个百花盛开、宛若仙境的移花宫了,最令我歆羡的是宫中人餐花饮露、仙袂飘飘,神态风度大概跟《庄子·逍遥游》中的姑射神人差不多吧。移花宫说不定也栽有紫藤,藤花说不定也是他们的美馔呢,我这样想着。
自那次结识紫藤之后,心心念念的事又多出一桩。前些年搬家,寓所自带花园,总算有地方种些花木,于是在侧院栽上了紫藤。今年疫情期间,值藤花盛放,我和母亲一起摘了几串藤花下来,按先生老家一带的做法,做成了藤花饼,入锅蒸了会儿,清香四溢;细嚼藤花,只觉胸中洒落无俗物。闲暇时,望着绕窗的紫藤出神,心想这般美好的花儿大约何时为人所知呢,于是想着深入了解一下紫藤。一查文献下来,发现这种藤本植物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蕴,跟交到了眉目如画才情出众的好友似的,了解紫藤愈深,欢喜愈甚。
“虎豆”是“紫藤”的别名吗?
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紫藤(Wisteria sinensis)为豆科紫藤属多年生落叶藤本植物,原产我国;茎左旋,枝较粗壮,嫩枝被白色柔毛,花冠紫色,花期4月中旬至5月上旬。据《中国植物志》载,紫藤是紫藤属(Wisteria Nutt)大家族中的一员,紫藤属藤本共约10种。另一种较常见的是多花紫藤(Wisteria floribunda),原产日本,我国已引进栽种;茎右旋,枝较细柔,初时密被褐色短柔毛,花冠紫色至蓝紫色,花期4月下旬至5月中旬。还有一种常见的是宗璞《紫藤萝瀑布》一文中的藤萝(Wisteria villosa Rehder),又名紫藤萝,原产中国;茎左旋,生枝粗壮,密被灰色柔毛,花的颜色稍淡于紫藤,花期5月上旬。
19世纪时,紫藤(Wisteria sinensis)经广东传入欧洲;1830年,德国学者西博尔德又将多花紫藤(Wisteria floribunda)引进了欧洲(西莉亚·费希尔《东方草木之美:绽放在西方的73种亚洲植物》,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紫藤在欧洲安家之后,深受民众喜爱,也极受文人、艺术家青睐。1911年,波兰新艺术风格画家爱德华·奥肯(1872-1945)创作了油画《盛放的紫藤》,这幅风景小品画描绘了一只小鸟落在盛放的紫藤上,风格灵动隽永。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1840-1926)以画睡莲著称,他也画紫藤。2019年,荷兰海牙市立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发现,在莫奈晚年创作的一幅《紫藤花》的颜料层下,隐藏着一幅《睡莲》。莫奈大概想尝试一些新的创作技法,但毫无疑问的是,跟睡莲一样,紫藤也是他所钟爱的绘画对象。
爱德华·奥肯《盛放的紫藤》,1911年
画中有画的《紫藤花》,莫奈
唐陈藏器《本草拾遗》始详录紫藤(Wisteria sinensis):“紫藤,味甘,微温,有小毒。作煎如糖,下水良。花挼碎,拭酒醋白腐坏。子作角,其中仁熬令香,著酒中,令不败酒,败者用之亦正。四月生紫花可爱,人亦种之,江东呼为招豆藤,皮著树,从心重重有皮。……京都人亦种之,以饰庭池”,其文大致介绍了紫藤的形态特征、食用及药用价值。关于紫藤,宋代的《证类本草》《嘉祐本草》、明代的《普济方》《本草纲目》等本草医学文献基本沿用了《本草拾遗》中的表述。
紫藤,又名“朱藤”“藤花菜”等。清人谢堃《花木小志》详录“朱藤”条,“藤花二色,紫色者名朱藤”,又载“其初舒放之际摘取,调面拌糖,炸食,颇适口”。明人朱橚《救荒本草》“藤花菜”条亦记载了紫藤入馔的做法。紫藤还可称作“葛藤”“葛花”,先生是河南新郑人,他老家一带是将“紫藤”称作“葛藤”“葛花”的。但需注意的是,“葛藤”一般指的是豆科葛属多年生落叶草质藤本植物,“葛花”是这种植物结的花蕾。在某些地区,蝶形花科豆薯属植物沙葛藤的花也称为“葛花”。
《中国博物别名大辞典》在“紫藤”条下还收录了“虎豆”“虎櫐”“欇”“猎涉”“㯿欇”等名称。这些名字看起来跟紫藤毫不相干,如何成了紫藤的别名?我们先找来晋人郭璞的《尔雅注》,《尔雅·释木》载“欇,虎櫐”,郭璞注:“今虎豆,缠蔓林树而生,荚有毛刺。今江东呼为㯿欇。音涉。”
我们再来读清人郝懿行《尔雅义疏》中的这段文字:“虎櫐即今紫藤,其华紫色,作穗垂垂,人家以饰庭院。谓之虎櫐者,其荚中子色斑然,如貍首文也。……云‘江东呼㯿欇’者,谢灵运《山居赋》云:‘猎涉蘡薁’,自注云‘猎涉字出《尔雅》’。是猎涉即㯿欇,皆音同假借字也。”郭璞指出“欇”、又名“虎櫐”的这种植物,在他那个时代被称作“虎豆”,当时在江东,也就是京都建康一带,又称之为“㯿欇”。他还略述了这种植物的形态特征,“缠蔓林树而生,荚有毛刺”。具这些形态特征的植物有很多,我们还是遽难判断《尔雅》所载的“欇”是哪一种植物。郝懿行的结论是:“欇”,也就是“虎櫐”,即“紫藤”。此结论缺少论证,难以信服。
《东方草木之美》,作者:西莉亚·费希尔,译者:王瑜玲,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
答案可从清人刘宝楠《释谷》中寻得。《释谷》:“欇,虎櫐,虎豆也;小者谓之貍豆。《尔雅》‘欇,虎櫐’,郭注‘今虎豆缠蔓林树而生,荚有毛刺,今江东人呼为㯿欇’,邵氏《正义》‘郭注《山海经》以櫐为虎豆,貍豆之属。‘貍豆’,一名‘黎豆’;虎豆,则虎櫐也。’《农政全书》‘黎豆,古名貍豆,又名虎豆。其子有点,如虎点之斑,故名。’《尔雅》所谓‘欇,虎櫐’,三月下种,蔓生,江南多炒食之。’案:邵氏以貍豆、虎豆为二,与《农政全书》异。崔豹《古今注》云‘貍豆,一名貍沙,一名猎沙。叶似葛而实大如李核,可啗食也。虎豆,一名虎沙,似貍豆而大,实如小儿拳,亦可食。’据此,则貍豆、虎豆本是一豆,特以大者名虎豆,小者名貍豆也。李时珍云‘貍豆,野生,山人亦有种之者。三月下种,蔓生,其叶如豇豆叶,但文理偏斜。六七月开华成簇,紫色,状如扁豆华,一枝结荚十余,长三四寸,大如拇指,有白茸毛,老则黑而露筋,宛如干熊指爪之状,其子大如刀豆子,淡紫色,有斑点如貍文。’……郝氏懿行《尔雅义疏》‘虎櫐,即今紫藤。其华紫色,作穗垂垂,人家以饰庭院,谓之虎櫐者,其荚中紫色斑然,如貍首文也’,亦以‘山櫐’当‘虎櫐’,与景纯注全不合。”
原来被称为“欇”“虎櫐”“虎豆”“猎涉”“㯿欇”“貍豆”“黎豆”的植物实际是一种豆科草本植物,本草文献中,唐代的《本草拾遗》始著录这种植物,“生江南,蔓如葛,子如皂荚子,作狸首文,故名黎豆。……人炒食之,一名虎涉,别无功”。
《中药大辞典》列“黎豆”条:“黎豆(《本草拾遗》),又名欇、虎櫐(《尔雅》)、虎豆、㯿欇(《尔雅》郭璞注)、狸豆(《古今注》)、巴山虎豆、鼠豆(《植物名实图考》)。一年生缠绕草本,全株被白色疏柔毛;花冠深紫色;荚果木质,条形,深棕色。”黎豆是一种豆科属蔓生草本植物,花也是紫色,形状似扁豆花,一枝结荚十余条,荚有毛刺,荚中子有斑纹。
由上可知,“虎豆”“虎櫐”“欇”“猎涉”“㯿欇”等指的是黎豆,跟豆科紫藤属植物紫藤无涉。而现今一些校注或工具书中,直接引用郝懿行的观点,误将这些当作紫藤的别名,这是需要注意的。比如,《植物名实图考校注》一书中,校注者在“黎豆”条下将“欇”注释为“紫藤”,不加辨析地径直引用了郝懿行的观点。《中国博物别名大辞典》“紫藤”条,“别名”一栏引用郝懿行《义疏》,误录了虎豆、虎櫐、欇、猎涉、㯿欇等5个名称。
隋唐以来“紫藤”一名在诗文中频频出现,据此可确定,该名称已是豆科紫藤属植物紫藤的专称了。而隋唐以前的文献中,只两处出现“紫藤”一名,一是《南方草木状》载“紫藤,叶细长,茎如竹根,极坚实,重重有皮,花白,子黑,置酒中,历二三十年,亦不腐败。其茎截置烟炱中,经时成紫香,可以降神”,据学者考证,《草木状》所载紫藤是一种香料植物,后名为“降真香”,是豆科黄檀属一种或多种藤本植物(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十四册《炼丹术和化学》第260页注2,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王祥红、王立志《降香与降真香本草考证》,《亚太传统医药》第15卷第1期,2019年);一是《玉台新咏》卷十所载南朝时期《有所思》中的一句诗“紫藤拂花树,黄鸟间青枝”,因隋唐以前文献例证较少,我们无法断定此处紫藤即本文所谈的豆科紫藤属紫藤。
上文已提及最早载录“紫藤”的本草文献是唐人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但这并不意味着唐以前这种植物无人知晓。《诗·国风·葛藟》为大家所熟知,起句“绵绵葛藟,在河之浒”中的“葛藟”即“葛藤”。《尔雅·释木》:“诸虑,山櫐。”晋郭璞注:“今江东呼櫐为藤,似葛而麤大。”清郝懿行《义疏》:“《说文》‘藟,艹也’,引《诗》‘莫莫葛藟’。……《广雅》云:‘藟,藤也。’《玉篇》云:‘今总呼草蔓延如藟者为藤。’是藤、藟皆兼草木二种。”可见“藤”这个汉字出现较晚,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文献里表示“藤”这种植物的基本皆用“藟”字。南北朝以来,文人作品中“藤”的用例慢慢多起来了。因此,先秦时代紫藤可能已被先人认识了,只不过那时候一些藤蔓植物包括紫藤在内大都被称作“藟”。
一架紫藤将俗世隔开了
郑逸梅《花果小品·紫藤》:“紫藤一架,春暮著花。生卧其间,可以忘世。”郑逸梅先生寥寥数语绘出紫藤风致,“生卧其间,可以忘世”,一语道出紫藤尤受文人喜爱的原因。翻阅文献,尤其是明清以降的诗文,可发现紫藤寄寓着一种超拔脱俗的精神。文人们或闲卧于紫藤架下,或于紫藤架下读书作诗,怡情养性,与世相忘。
林风眠《紫藤》,20世纪60年代初期
明人陈继儒《题孙世声紫藤》:“㕍洲孙先生曾手栽紫藤,仅如寸草,为邻儿摘去,几无萌芽。郎君侍洲公乃复引之而上,今将六十馀年,遂能荫及半亩。乃孙世声构一室于藤下,大可围四掌,其根如瘿鉢,其枝如悬槌,其花如绛雪红霞……余每造藤下,弥日忘返,徙倚凉阴香欲寒而余不去,直以主人真堪晏坐,是藤又借主人为胜也。”眉公自言“每造藤下,弥日忘返”,情性之清逸跃然纸上。
那一架藤萝是清人孔尚任“朝朝吟啸”的良伴。紫云翠幄中,他终于可以稍稍从俗务中抽身出来,安心修改他的《桃花扇》。康熙二十五年,孔尚任随工部侍郎到淮阳,疏浚黄河入海口。二十九年,湖海生涯结束,返京,复任国子监博士。返回京师第五年,亦即康熙三十三年,孔尚任在一首诗里写道:“朝朝吟啸此堂阶,一架藤萝惬旅怀。”“此堂”指的是“岸堂”,孔氏在京时所居寓所。康熙三十六年,迁任户部主事,宝泉局监铸。这一年,作诗云:“衙散朝回亦不忙,敲门诗客趁晴光。海波巷里红尘少,一架藤萝是岸堂。”自注:“予出使海口,著《湖海集》,每有漂泊之感。还京后,又寓海波巷,心窃厌之,阮亭先生为题‘岸堂’。”
张崇琛《“岸堂”发微》一文提到,近四年的湖海生涯,孔尚任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每有漂泊之感”,故以“岸”名其居室,绝云水之缘;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孔尚任看尽了官场腐败和民生凋敝,自身非但不能有所作为,还时有被“排挤倾陷”的危险,对仕宦生活便渐由憧憬转为厌倦甚而惧怕了。返京后,孔尚任“杜门抱膝,邈若空山,弹琴吟风而外无他好”,“于人世进退之故,泛泛若海鸥之无心”。他将居室命名为“岸堂”,以示“宦海无边,回头是岸”,友人王士祯为他题写了“岸堂”匾额。他在一架藤萝的陪伴下,醉心于戏剧、诗文创作,著作等身。岸堂院子里的那架藤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出世精神的象征。
清人李慈铭也爱那一架紫藤花开。光绪七年,也就是他补户部江南司资郎的第二年,四月初七日那天,“竟日坐紫藤花下,阅《古微堂诗集》”。有着一架紫藤的院子是他租赁的,院子里花木葱茏则是他苦心经营的成果。他在题为《立夏前一日紫藤花盛开,轻阴微雨坐花下作》诗里颂紫藤:“十年赁此舍,隙地皆种花。辛勤几心力,偿以三春华。花树幸长成,白发弥自嗟。西轩一朱藤,拂拭尤倍加。垂阴几盈亩,夭矫争龙蛇。缚架出檐外,葳蕤天半霞。纍纍万紫琼,因风被璎珈。吹香及初夏,擢鲜殿春葩。轻阴照横几,碎英点烹茶。扶持紫云立,不随柳枝斜。清绝日宴坐,林幄如山家。何当围朱阑,映以碧窗纱。”
光绪十三年四月初八日,“坐藤花下啜茗,是日得诗三首”,其一为《自城南寺归坐紫藤花下作》:“暂得入外赏,暝色催遥岑。归路喜不远,有宅枕街阴。入门灯未上,三径若已深。虽云赁庑居,辛苦成山林。紫藤覆西屋,垂花若朱綅。偶然设横几,坐待归巢禽。花香在近远,好风能嗣音。簾端新月上,所惜无瑶琴。”李慈铭学识渊博,自视甚高,无奈仕途潦倒,沉浮冷衙。为官之外,他寄情于诗文,以消胸中块垒。从他留下来的文字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竟日坐紫藤花下”“竟昼坐藤花下”“坐紫藤花下作”,那一架藤花将俗世隔开了,他在紫藤花下,“是非两忘羊,万古同尘埃”(元人叶天趣《感寓》),著文赋诗,澡雪精神。
文人也喜绘紫藤。从题画诗可知,紫藤往往承载着一种高蹈隐逸的生活态度。元人王蒙所绘《茅屋讽经图轴》,经明代潘允端、都穆、张丑、清代钱载等人鉴藏,惜今已不存。题于画上的题画诗著录于清人葛金烺、葛嗣彤所撰《爱日吟庐书画丛录》和钱载《箨石斋诗集》中,题款曰:“客来客去吾何较,山静山深事亦无。一卷《黄庭》看未了,紫藤花落鸟相呼。至正八年秋七月二日,叔明为表甥崔彦晖画并题。”
王蒙(1308-1385年),字叔明,号黄鹤山樵,与黄公望、吴镇、倪瓒并称“元四家”。擅书法,能诗善文,尤工山水画。元末明初,社会动荡,王蒙弃官隐居于临平(今浙江余杭临平)黄鹤山,参禅学道,远离尘嚣。由他的题画诗可知,他这幅画描绘了茅屋内外的情景:茅屋内,文士手持一卷《黄庭经》在细细品读;茅屋外,山静似太古,藤花满檐,花落无声,唯啾啾鸟鸣。山居幽闲,无俗事侵扰,偶有访客,来去不必计较。画面清寂,而题在画上的这首诗则是延宕在画面之外的袅袅余音,向我们诉说着一种避世静修的生活。“紫藤花落鸟相呼”,以动衬静,淡淡几笔勾勒出世外桃源般安宁的生活。王蒙笔下的紫藤,深藏着那个时代文人的高情逸思。
“香钵分甘露,田衣挂紫藤”
紫藤在内的一些藤本植物,或附乔木而生,或缘花棚而茂,或屈曲蜿蜒于深山幽谷,或纷披摇曳于小院闲窗,不管其生长于何处,似乎都具有一种清逸出尘的气质。倘若往莽莽苍苍历史的云海中投上一瞥,我们发现,大约从魏晋时代起,藤被认为是通往净土仙界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关于这点,矢嶋美都子《关于庾信“游仙诗”中所表现的“藤”》一文已论及,下文试述其详。
魏曹植《七启》:“玄微子隐居大荒之庭,飞遁离俗,澄神定灵,轻禄傲贵,与物无营,耽虚好静,羡此永生。……于是镜机子攀葛藟而登,距岩而立,顺风而称曰:‘予闻君子不遁世而遗名,智士不背世而灭勋……’”曹植在这篇辞赋中虚构了玄微子和镜机子两位人物,玄微子超凡脱俗,与世无争,隐居大荒之庭,修真养性,“玄微”二字含“深隐”之义,代表道家的出世思想;镜机子则是洞鉴造化、明断机运的儒士,崇尚经世济民的入世观念。镜机子想劝说玄微子立勋留名于世,于是去访问隐居在大荒之庭的玄微子,而隐士所居的地方是需要通过“攀葛藟”才能抵达的。
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 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 灵仙之所窟宅。……跨穹隆之悬磴,临万丈之绝冥。践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揽樛木之长萝,攀葛藟之飞茎。虽一冒于垂堂,乃永存乎长生……”,可见净土仙界不是那么容易进入的,得把揽樛木之萝,攀援葛藟之茎。孙绰创作此赋之前并未亲历天台山,他在序言中提到,“然图像之兴,岂虚也哉”,由此推测,此赋很可能是他在欣赏天台山画作的基础上写就的。又因久居会稽,耽于山川之美,孙绰常常涉水登山,积累了不少游览经验,故此赋虽虚拟游山,然情真意切。他本人崇尚老庄玄学,兼具佛教思想,在赋中铺陈了登山觅仙的经过,借山水而谈佛道,表达了避世去俗的愿望。那要如何才能抵达作为玄圣游化之所和仙人居处之地的天台山呢?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在文中也表示,通过攀援“葛藟之飞茎”抵达。
前文已述及,“藟”即“藤”,“藤”这个汉字出现较晚,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文献里表示“藤”这种植物的基本都用“藟”字。南北朝以来,文人作品中开始出现“藤”的用例,如:梁朝何逊《渡连圻诗二首》其一:“此山多灵异,峻岨实非恒。……百年积死树,千尺挂寒藤。”范云《登三山诗》:“仄径崩且危,丛岩耸复垂。石藤多卷节,水树绕蟠枝。”与庾信同时代的王褒作《过藏矜道馆》,其诗云:“松古无年月,鹄去复来归。石壁藤为路,山窗云作扉。”不难发现,这些作品中的野藤似乎已成了审美意象,烘托出一种幽寂清旷的氛围。后梁萧詧《游七山寺赋》云:“既攀藤而挽葛,亦资伴而相提。”到了后梁宣帝萧詧这里,藤依然被看作是通往仙境的工具。
大约隋唐之后,随着园林住宅的发展,人们开始在庭院中广泛种植藤本植物。藤从世外山林来到人间院落,出尘之姿依然,另逗人遐思的是其花色之美。因此,从唐代开始,涌现出大量吟咏紫藤的诗文。比如,李白《紫藤树》:“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此诗绘紫藤优美之姿,用语省静,蕴藉有味。白居易《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慈恩春色今朝尽,尽日徘徊倚寺门。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全诗以景抒情,情寓景中,心头叹息仿佛落在诗里的一滴墨,于字里行间渐渐晕染开来,虽惜春不尽,然终究留春不得。李德裕《忆新藤》:“遥闻碧潭上,春晚紫藤开。水似晨霞照,林疑彩凤来。”晚唐名相李德裕为政深陷“牛党之争”,日常竟也有小儿女般温柔的情怀,将紫藤比作“晨霞”“彩凤”,可见其也是极爱紫藤的。
宋人沈括《补笔谈》谈到紫藤:“天下皆有,叶如槐,其花穗悬,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师人家园圃中,作大架种之,谓之‘紫藤花’者,是也。实如皂荚。”不过宋代关于紫藤的诗文不太多,“绿树村边停醉帽,紫藤架底倚胡床。不因萧散遗尘事,那觉人间白日长”,像这样将紫藤入诗的佳构在宋代真如吉光片羽了。宋人吴可《藏海诗话》:“白乐天诗云:‘紫藤花下怯(渐)黄昏’,荆公作《苑中》绝句,其卒章云:‘海棠花下怯黄昏’,乃是用乐天语,而易‘紫藤’为‘海棠’,便觉风韵超然”,宋人对紫藤的态度于此可窥一斑。
到了明代,藤似乎又成了通往世外的工具。从历史上看,与大唐帝国的外向扩张相反,朱明王朝则内向收敛,经济上退缩保守,而政治上变本加厉地实行中央集权。清朝虽不乏改革,但从总体来看,因袭明朝。在明清文人的笔下,藤又接续了六朝以来的高标神韵,不知是否与国家本身的内敛气质有关联?
明人叶盛《水东日记》卷八载:“衣和庵主,苏州昆山人也。隐居雪窦之栖云,畜二虎,恒跨之以游。后徙二灵终焉。初,雪窦妙高峰左千丈山巖巅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临不测,乃蟠结成龛,为藏修之所,故号栖云。”这里记载了一位善驯虎的僧人,他将山巅藤枝蟠结成龛,并命之为“栖云”,作为藏修之所。僧人隐士所居的地方,往往都栽有紫藤。如:明人刘士亨《贺法相寺海纳庵上人》诗云:“衲挂紫藤惊鼠窜,钵分沧海毒龙降。怀香欲叩毗尼藏,寸筵临钟不易撞。”诗僧圆复《赠无生祝发》曰:“香钵分甘露,田衣挂紫藤。从今翠微里,添个白云僧。”清人陈志襄《访隐者不值》:“采药不知何处去,疏篱开遍紫藤花。”
“紫藤里有风”
魏晋以来的文论家很看重外物对人内心情感的感发。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都从情感发生论的角度阐明了作者进行文学创作往往跟“外感于物”有关。窈窕摇曳于深深庭院中的一帘帘紫藤,自然勾连着世间许多情。
许浑《紫藤》:“绿蔓秾阴紫袖低,客来留坐小堂西。醉中掩瑟无人会,家近江南罨画溪。”许浑是晚唐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他这首《紫藤》读来颇令人动容,叫人想起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句话来,一样心事浩茫,一样清思如雪。清人黄叔灿评:“对花忆家,思致渺然。”近人俞陛云论:“此作句秀而音婉,其命意所在,可就第三句观之。当藤花盛放,紫云翠幄中,留宾欢醉,而忽悠然掩瑟,感会意之无人。盖忆罨画溪边往事,风景依稀,未得逢人而语,故罢弹惆怅耳。”
诗人借盛放的紫藤发思乡之情,那种忆往昔岁月无限神伤而寂寂无人能会的心情,那种孤独悲凉的况味,似乎也只能闲闲地说与一串串垂挂着的藤花听了。试想一下吧,倘若你孤身一人漂泊在外,春日里忽遇蓬蓬紫藤,照人眼眸,你内心深处那根思乡的弦刹那间被拨动了,你想起老家门口的那株了,想起更多“灯火闲坐,家人可亲”的往日温柔时光,万般感慨,顿时齐上心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那些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今古攸同。
“平堤一色绿初铺,四月江乡画不如。遥忆风前小儿女,紫藤花下读家书”,这是乾隆年间担任翰林编修的洪亮吉寄给他家人的诗。寒食日早得家书,在紫藤花开的四月里,他给我们留下了如此明净莹洁的诗句,拳拳爱子之心透纸而出。全祖望重情守义,他在《陆茶坞墓志铭》一文中,回顾了与好友陆锡畴的交往:“予之交茶坞也,以祁门马嶰谷,一见即倾倒。尝曰:‘谢山无终老山林理’,不知其言之不验也。予游岭外,一病几死,病中梦过水木明瑟园,与君坐紫藤花下,啖莼羹,君复以酒困予,予曰:‘此伏波曳足壶头时,不复与君抗也。’醒而异之,以为侥幸生还,一践此景,岂知茶坞已弃我而去乎!”谢山与茶坞情好甚笃,茶坞家那架紫藤见证着他俩的友情,想来他俩常常在紫藤花下饮酒赋诗,否则谢山病中不会无缘无故梦到这一场景吧。
紫藤花架,图片/IC photo
读《白香山集》,我们发现白居易常将紫藤入诗。《宿杨家》:“杨氏弟兄俱醉卧,披衣独起下高斋。夜深不语中庭立,月照藤花影上阶。”此首作于元和二年春,白居易时任周至尉,与靖恭杨家关系亲密。元和三年,白居易37岁,在母亲陈氏的授意下,与杨汝士之妹完婚。有学者推测《宿杨家》这首诗委婉地表露了诗人对杨汝士之妹的爱慕:杨氏兄弟醉倒了,而诗人深夜独立于中庭,默默凝视着阶上藤花的影子,心里或许盼着台阶上出现杨汝士之妹的身姿(平冈武夫《白居易和他的妻子》,选自《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三秦出版社,1995年)。
结合诗人早年的情感经历来看,我们更愿意相信诗人月夜下独对紫藤的那一刻怀想的是初恋情人湘灵。白居易早年与一位名叫湘灵的姑娘倾心相爱,但限于门第观念,二人未能结秦晋之好,因此拖延耽误了婚事。白居易对湘灵怀着真挚的感情,我们可从诗句中感受到他对湘灵深厚的情意,比如《寄湘灵》“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干独自愁”,《长相思》“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冬至夜怀湘灵》“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等。
或许缺憾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圆满,湘灵是诗人心灵深处永远的恋人。任岁月流逝,任世事变迁,诗人对湘灵的思念有增无减。“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诗人四十岁那年,在秋雨残灯的夜里又想起了湘灵,写下了这首《夜雨》;“中庭晒服玩,忽见故乡履。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因思赠时语,特用结终始。永愿如履綦,双行复双止。……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可嗟复可惜,锦表绣为里。况经梅雨来,色黯花草死”,诗人四十六岁那年,有次在晾晒服玩时忽见湘灵赠送的鞋子,写下了这首《感情》。我们再来读《宿杨家》,整首诗带给人的感觉仿佛于寂寂永夜听闻幽咽笛声,诗人的惆怅犹如春夜中的紫藤,寂然垂挂着,无人能解。
汪曾祺
汪曾祺短篇小说《鉴赏家》有一段关于紫藤的对话很有味,“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叶三说:‘紫藤里有风。’‘唔!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对极了!’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乱。’”“紫藤里有风”,汪先生可谓紫藤的知音,极冲淡极简净的一笔,将紫藤风致都描出来了。紫藤花作蝴蝶形,成群成串如璎珞般连缀在一起,深深浅浅的紫如烟似雾氤氲一片,微风吹过,一串串藤花轻轻摇曳,簌簌飘落,像一个春宵的梦。藤枝交错纷披,藤叶翠色娟娟,藤花绰约可爱,也难怪紫藤枝枝叶叶总关情了。清人莫友芝写过一首《荷叶杯》:“回首紫藤花底。凝睇。晚色使人愁。柔枝胜系月如钩。休么休,休么休。”一对恋人相会在紫藤花下,互诉衷肠,紫藤再一次见证了爱情,怎奈聚散匆匆,相会无期,暮色里徒留一声叹息。
朱冰蝶《紫藤花下》,1921年
稍读过西方文学史的都知道,在西方,玫瑰是爱情的象征。而我一直以为,紫藤其实很能代表爱情,既具袅袅萦怀的温软,又见世世相随的坚定。紫藤花开,串串流泻而下,说不尽的娇柔缱绻,紫藤枝干则盘曲交错,如《花经》所述“缘木而上,条蔓纤结,与树连理,瞻彼屈曲蜿蜒之伏,有若蛟龙出没于波涛间”。有一首客家山歌就“藤缠树”意向反复言说,极缠绵地表达了爱情的忠贞不渝:“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藤生树死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不过凡事都要讲究适度,爱情也不例外,倘若走了极端,不留一点儿私人空间,紧紧交缠,爱情终会被绞死吧。
钱新祖《公案、紫藤与非理性》一文谈到,“有句无句,如藤倚树”,这是宋朝圆悟禅师给弟子参解的一则公案。《出曜经》云:“其有众生堕爱网者,必败正道,犹如葛藤缠树,至末遍则树枯”,佛戒“贪、嗔、痴、爱”,在佛家看来,“堕入爱网”者如同被紫藤缠绕的树一样,烦恼至终。其实这里的爱,指的是对欲望的一种偏执追求吧。禅宗语录中,常常能见到“葛藤”,将藤枝缭绕不清、相互纠缠比喻为是非烦恼。《景德传灯录》卷一二《睦州龙兴寺陈尊宿》:“新到僧参,师云:‘汝是新到否?’云:‘是。’师云:‘且放下葛藤,会么?’云:‘不会’。师曰:‘担枷陈状,自领出去。’”人生如寄,身若微尘。当遇烦恼时,须如这则公案所启示的那样清明,“放下葛藤”,自求解脱。
紫藤绕棺
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六“紫藤绕棺”条载:“宋方匀《泊宅编》曰:吴伯举舍人知苏州日,谒告归龙泉迁葬母夫人,已营坟矣。及啓堂,见白气氤氲,紫藤绕棺,急复掩之。术人视殡处,知是吉地,因即以为坟,然颇悔之,舍人竟卒于姑苏。又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曰:上舍伯祖巽旧葬惹山,后忽卜兆于丁村,遂迁葬焉。其中紫藤幡固棺上,或云穴有紫藤,此吉征也,竟斫藤迁之,自后其家浸衰。余门生徐花农太史母郑夫人,葬如皋,后其父若洲先生卒,启而合葬焉,见有藤蟠绕棺之四周。后花农既贵,欲迁其父母之柩还葬杭州而未敢决。余于书籍见此二事,因记之以告花农。”
此则笔记很有意思,术人当指擅长堪舆者。据《史记·日者列传》,术数有七家,堪舆家为其中一家;《汉书·艺文志》载《堪舆金匮》十四卷,可见“堪舆”在汉代已成一门学问。堪舆家,俗称“风水先生”。古人在确定住宅、庙宇、墓地等位置时,风水先生会综合考虑山水、树木、气候等诸多因素,做出吉凶判断。
我们来看此则笔记,俞樾门生徐花农想将父母灵柩迁葬杭州,但因紫藤绕棺,不敢贸然迁葬;俞樾刚巧从《泊宅编》《闲窗括异志》中读到无视紫藤绕棺而迁葬最终招致厄运的二则事例,便记下来转告花农。由此可见,紫藤绕棺,在古人看来,是一种吉兆;倘若斫藤迁葬,势必会遭受报应。又如明人白胤昌《容安斋稣谭》卷六所记载的事例:“余曾祖妣吕淑人葬时,启曾祖司徒石渠公兆,见紫藤如带,束其柩十馀围,皆讶为瑞,是年司空公以解元联第。”
清人冯班《钝吟杂录》卷一《家戒》列举了一则因斫藤迁葬而毁运的例子:“有一郭春卿,其父葬得吉壤,生春卿,读书数行俱下,不过二遍则暗诵矣。后为恶人所误,言不吉。发之,紫藤缠棺,斩之,流汁如血。春卿归读,读书强记不复如前矣,竟以一老青襟卒。”
征兆,是古老的预知未来的一种迷信手段。宋兆麟《巫与祭司》一书谈到,人类早期社会,将自身与万物混为一体,“自己有灵魂,万物也有灵魂,而且能互相转化……人与万物联系起来了,进而发展为自然崇拜,认为自然现象的变化,必然引起主观行为的变化,两者有一种因果关系。所以,自然和人体的征兆,是自然神的一种意志表现,从而警告人应该慎重从事自己的活动”,可见征兆迷信是一种古老的信仰。古人视一些植物为神灵,将植物现象看作吉凶的预兆,与人事祸福相关联。古史传说、神话中包含不少植物兆的例子,如桑榖共生、朱草现、二树连理等。正史中的《五行志》《符瑞志》《祥瑞志》《灵征志》《灾异志》等,记载了大量植物预示吉凶的事例,笔记野史中更是所在多有。
李桦《紫藤》,1935年
紫藤绕棺,可谓植物兆中的一种。元人王恽《玉堂嘉话》载:“唐太真改葬祖墓,上有紫藤一株,阴影甚茂。既伐去,藤流赤津如血。不数年,刘氏灭之殆尽,因以往岁改葬。”这里的太真,指的是盛唐诗人刘太真。刘太真仕途比较平坦,深受唐德宗器用,在他从政生涯中,曾连续两年执掌贡举,为朝廷选拔人才,怎料有人举报他选士不公,偏袒大臣贵近子弟,因此遭言官弹劾,被贬为信州刺史,后在任上去世。《新唐书·列传》卷二百三《刘太真》:“刘太真,宣州人。善属文,师兰陵萧颖士。……迁礼部,掌贡士,多取大臣贵近子弟,坐贬信州刺史,卒。”
关于他被贬信州刺史,其实有另一种说法。《地理新书》卷九“刘太真”条云:“耳目记唐德宗时,侍郎刘太真以先夫人权庴在江南,未附大茔,表请暂归。既行,桑道茂善于太真,令其门人随往觇之,仍戒之曰:‘吾观刘门宇气色方旺,常疑其先茔择佳地。汝往看,彼物色或有异状。即窃观之,勿吏移动。’既至,果有紫藤盘偃如盖,周覆于墓。因坚请太真不宜启发,刘公表乞归葬,不敢不开。及开视之,则紫藤根数茎圆围其柩,垂间于冘中,缠束壮固,不可摇动,乃悉伐之,而藤根流液,色若鲜血。须臾穴中深数十。桑氏门人为之抚膺。太真既北还,寻贬信州刺史。”想来这便是王恽《玉堂嘉话》中那段记载的出处了,虽不免附会,不过我们从中可知古人是何等坚信紫藤绕棺之预兆了。
《文化人类学》,作者:林惠祥,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1年9月
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中谈到,“在隆冬时锢闭的生命一到春来便能茁叶开花结果,而且微风吹来枝叶间似乎都会发出叫声,‘这岂不是也有精灵的征验吗?’在原始民族观之,植物和动物都有同人类相似的感情与意志。……森林中的居民以林木与他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尤常以树木为崇拜的对象。……奥夸的土人不敢用几种树木做独木艇,因恐树木的精灵会杀害他们。暹罗人在砍伐‘答健’木以前必先祭以饼和米。奥国的乡人当纵斧之前必先向树木求恕。……人的幸运与其收获和植物极有关系,所以发生了许多媚求植物精灵的风俗”,可见古人将紫藤绕棺视作吉兆,或许跟植物崇拜有关。紫藤花与枝干都满载着生命的力量,藤花纂纂迸溅濯濯辉光,藤枝则坚强苍劲,一旦有所附缘,便盘曲交缠而上,极富生命力。古人大概因此将紫藤视作“生命树”,“紫藤绕棺”象征着福泽绵绵不绝。
藤花入馔
邓云乡曾说过,“懂得吃花,正是我们懂得生活的艺术”。历史上的中国是诗的国度,从来也是懂得生活艺术的国度。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先人已撷花入馔了。“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以餐花表明心志,可见我们国家花馔的历史源远流长。
紫藤花入馔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人陈藏器编撰的《本草拾遗》,“紫藤,味甘,微温,有小毒。作煎如糖,下水良”。我疑心紫藤花入馔是由僧人流传开的。晚唐诗人皮日休《夏初访鲁望偶题小斋》:“半里芳阴到陆家,藜床相劝饭胡麻。林间度宿抛棋局,壁上经旬挂钓车。野客病时分竹米,邻翁斋日乞藤花。踟蹰未放闲人去,半岸纱帩待月华。”胡以梅评曰:“‘竹米’‘藤花’,皆野逸之品。僧家常以紫藤花作油酱,味佳。”元代僧人释来复《采藤花》诗云:“山味有佳品,紫藤春著花。……自知藜藿肠,食淡良非奢。”
《本草拾遗》辑释,作者: (唐)陈藏器撰/尚志钧辑释,版本: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1月
紫藤花可作馄饨馅,元人倪瓒《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煮馄饨”条曰:“细切肉燥子,入笋米,或茭白、韭菜、藤花皆可。以川椒、杏仁酱少许和匀。”这种馄饨馅的具体做法是:将肉切碎,拌入米粒大小的笋丁,或拌入茭白丁、韭菜末、藤花末都行,再加入少量的川椒、杏仁酱,搅拌均匀。将紫藤花用作馄饨馅,这在今人看来,真真风雅至极。明人高濂《遵生八笺·馔服食笺》亦谈到藤花可作食馅,此笺“藤花”条载:“采花洗净,盐汤洒拌匀,入甑蒸熟,晒干,可作食馅子,美甚。荤用亦佳。”
困难时期,紫藤花可用作度荒食材。天地有大美,生活再艰难落魄,只消端出盈盈一盘藤花,生活的底色依然明媚清朗。明太祖第五子朱橚《救荒本草》“藤花菜”条记载了当时河南一带藤花入馔的做法:“采花煠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微焯过,晒干,煠食,尤佳。”紫藤花蕊还可助茶提香,可下酒。清人查慎行听闻藤花此妙用后,立马尝试,并满心欢喜地记录了下来,“或云紫藤花蕊可瀹以点茶、下酒,从自怡园采一斗许,试之,香味果清绝”(查慎行《敬业堂集》卷三十八)。
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榆钱糕”条提及“藤萝饼”,曰:“三月榆初钱时,采而蒸之,合以糖面,谓之榆钱糕;四月以玫瑰花为之者,谓之玫瑰饼;以藤萝花为之者,谓之藤萝饼,皆应时之食物也”。邓云乡极爱这种藤萝饼,特意撰文细谈,“藤萝饼的馅子,是以鲜藤萝花为主,和以熬稀的好白糖、蜂蜜,再加果料松子仁、青丝、红丝等制成。因以藤萝花为主,吃到嘴里,全是藤萝花香味,与一般的玫瑰、山楂、桂花等是迥不相同的”。他在文中还谈到了老北京一道家常菜——“藤花块垒”,且看具体做法:“拾半篮藤萝花,回家洗干净,拌上干面粉,上锅一蒸,熟后起油锅,加点盐和葱花一炒,可说是清香扑鼻,别有风味。”
藤花开了,却无人知晓
东邻日本也是极爱紫藤的一个国度。东京、京都等地,每一座庭院,几乎都少不了一架紫藤。东京的龟户天神社有“东京第一赏藤胜地”之美称,这里的紫藤江户时代已负盛名,每逢花期,人们争相至神社赏花。翻开日本文学史,我们发现,日本文学,尤其平安朝文学处处可见紫藤的身姿,作者借藤花或表相思意,或发思乡情。《万叶集》《八代集》《枕草子》《伊势物语》《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对紫藤的描绘所在多有。
《万叶集》载大伴四纲撰写的一首和歌:“藤枝垂新英,紫波荡漾馨风兴,看花目光凝。欲向旅人询乡情,君能不忆平城京。”作者与大伴旅人同为平城京出身,同在九州赴任。大宰府藤花盛放,作者思乡之情顿起,想起家乡平城京紫波起伏的情景,于是写了这首歌。又如山部宿祢赤人的一首和歌,“为永吾思,昔植于家;窈窕藤浪,今见其花。为表相思意,户外把藤插;藤条形似浪,今已满著花”,相思意如藤浪缭绕不绝。《伊势物语》记载了一则小故事:“从前有一个人,住在一所衰颓了的屋子里,庭中种着藤花。这庭院中别的花木一点也没有,只有这藤花美妙地开着。三月末有一天,主人不顾春雨霏霏,亲手折取一枝藤花,奉献给某贵人,附一首诗曰:藤花开过也,春色已阑珊。冒雨殷勤折,请君仔细看。”冒雨折藤花赠友人,极平常的小事,然言浅意深,读来如清夜于幽窗赏竹影。
安藤广重《龟户天神社的紫藤花》,1856年
关于藤花和日本文化,川端康成有过一段妙评:“我觉得这种珍奇的藤花象征了平安朝的文化,藤花富有日本情调,且具有女性的优雅,试想在低垂的藤蔓上开着的花儿在微风中摇曳的姿态,是多么纤细娇弱,彬彬有礼,脉脉含情啊。它又若隐若现地藏在初夏的郁绿丛中,仿佛懂得多愁善感。……日本吸收了中国唐代的文化,尔后很好地融会成日本的风采,大约在一千年前,就产生了灿烂的平安朝文化,形成了日本的美,正像盛开的‘珍奇藤花’给人格外奇异的感觉。”紫藤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得益于日本对中国唐代文化的接受,特别是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我以为也跟日本人独有的纤细的感受有关。
《白氏文集》九世纪中期传入日本之后,深受当时文人喜爱。白居易《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被载入《千载佳句》和《和汉朗咏集》,成为文人争相传诵模仿的名句。藤原明衡《闰三月尽日慈恩寺即事》“丹心初会传青竹,白氏古词咏紫藤”,惟宗孝言同题之作“白氏昔词寻寺识,紫藤晚艳与池回”,岛田忠臣紫藤诗“料量紫茸花下尽,家香更作国香飞”等,皆化用白居易诗。紫式部想来也是熟诵《白氏文集》的,小说《源氏物语》多处引用白居易诗歌,特别是《藤花末叶》这一卷,不着痕迹地完美化用了“紫藤花下渐黄昏”这一句诗意,相关研究可参见日本学者中西进所撰写的专著《与白乐天》。
《十六个汉字里的日本》,作者: 姜建强,版本: 新星出版社2019年4月
在日本人看来,从植物中提取的紫色素的颜色是紫色,而由赤和青混合而成的则是伪紫色;紫色,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最具安静清艳高贵的气质(姜建强《十六个汉字里的日本》,新星出版社,2019年,第49页)。清少纳言《枕草子》“女子穿白绫单衣,外面加披紫色薄衣,最是清雅”,“凡是紫色的东西,都很漂亮,无论是花,或是丝的,或是纸的”,大抵表达了日本人对紫色作为理想之色的一种偏爱。
紫色,在日本被视作最高贵色。推古十一年,圣德太子借鉴儒家学说和隋唐的做法,制定并颁布了“冠位十二阶”制,以紫色配最高位大德。紫色,亦被视为因缘色。《源氏物语》中,藤壶妃子、紫姬与主人公源氏都有情爱关系,她俩的名字都与紫色有关。日文辞典《广辞苑》释“紫之缘”为“缘分起则情爱至”,紫式部将小说的灵魂织入名字中,藏起行文的针脚。藤壶妃子居住在飞香舍,离天皇的清凉殿最近。因院子里植有紫藤,飞香舍又称“藤壶”。藤壶妃子身份高贵,得蒙皇宠,能住在飞香舍不难理解了。我们也知道,藤壶妃子是源氏心目中永恒的恋人,源氏无法拥有她,但心头早已被紫藤一般的爱缭绕,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她的影子。可见紫式部将藤壶妃子的寝殿安排在栽有紫藤的飞香舍,以紫藤喻藤壶妃子,是别具深意的。
随着五月逝去,藤花也将忽而落尽。尘世中的我们,今年可曾与璎珞矜贵的藤花相会?说及相会,想起林徽因《藤花前——独过静心斋》这首诗了。如果说人生是一条河流,那么或缓或急流过生命的河床时,难免会激起莫可奈何的哀伤吧,如同诗作诉说的那样,“紫藤花开了,轻轻的放着香,没有人知道”。
紫藤花开了,
轻轻的放着香,
没有人知道……
紫藤花开了,
轻轻的放着香,
没有人知道。
楼不管,曲廊不做声,
蓝天里白云行去,
池子一脉静,
水面散着浮萍,
水底下挂着倒影。
紫藤花开了,
没有人知道!
蓝天里白云行去,
小院,
无意中我走到花前。
轻香,
风吹过花心,
风吹过我,——
望着无语,紫色点。
何凌霞/文
走走/编辑
贾宁/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