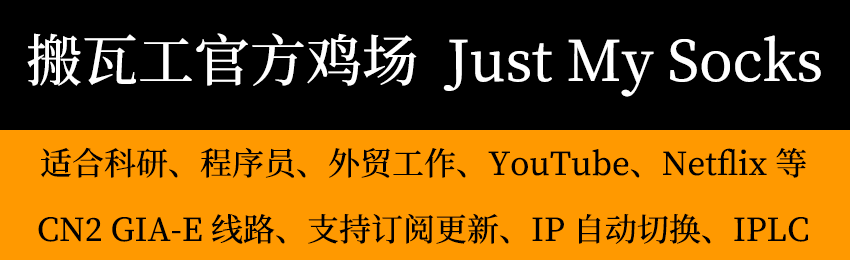
编前语:许渊冲(1921年4月18日-2021年6月17日),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曾荣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等。许渊冲先生曾在张家口工作生活过, 时值许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特邀张家口籍出版人付帅, 撰文回忆和许先生的点滴过往,以为纪念。
付帅
初识许渊冲先生是在2010年9月,彼时我刚到外研社工作,恰好有机会陪领导去许家拜访,缘由是我们有意策划出版许先生的全集。第一次拜访对许老尚无深入了解,看到他给我的名片上写着 “书销中外百余本 诗译英法唯一人”,顿感此人好大口气!回来在网上搜索许先生简介,才发现名片上的话绝非虚言,初见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
因全集之事,帮着许师母梳理版权,发现问题多多,想在短期内做“全集”,存在很大的侵权风险。于是,我们当时只签下《逝水年华》这本许老自传,暂时放弃做全集的念头。不过,作为法学院毕业的我,还是善意的提醒许老夫妇,哪怕没精力顾及其他,合同只签 “非专有”,也会给自己避免很多版权方面的麻烦。后来,二老基本遵循我的建议,即使不看合同的大部分条款,但一定会注意到“非专有”的约定。还记得许先生2019年11月应邀到北京外研书店做客,送他回去的路上,我问起版权之事, 他立即说:“我记得呢!非专有”,让我颇为感动和欣慰。
和许先生和师母来往时,发现有不少共同的缘分:许先生在西南联大读本科,我在云大读本科,虽然时间相隔半世纪以上,但谈起云南的美食、风物都颇怀念;许先生是北大的名教授,我是北大的研究生,都是北大人;我是张家口人,许先生当年曾经服务的香山外国语学院曾一度也 “疏散”到张家口,连许先生的独子许明也出生在张家口。此外,照君师母是石家庄人,也有地缘上的亲切感。总之,我与二老交往中越发亲近,加之许明先生不在身边,我便乘逢年过节,尽量做些“有事弟子服其劳”的义务。
照君师母性格活泼开朗,对人热情,大部分外联事宜都由她办理,我开玩笑的说,她是许老的金牌“经纪人”,师母也欣然接受。有时陪同事、媒体朋友去探望许老,接洽之后,我便和师母在旁边闲聊,她会骄傲的谈起远在美国的儿子、或者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以及许先生的伟大。
许师母在热爱许先生之外,甚至还有些崇拜,在聊天时总是称呼“许先生”而不名。有一小事印象深刻,有天晚上去许家做客,二老拿出凤凰卫视刚给许先生拍的纪录片光盘给我看。其中有先生谈起大学时候因爱情而痛哭流涕的镜头,我还“担心”师母的反应,哪知她如既往的平静,让我很是意外。
2017年初,许先生因为走进“朗读者”节目,意外地“走红”,一时间出版社、媒体、粉丝们纷至沓来,变得越来越忙,于是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再登门。某天接到师母电话,叫我过去教她使用“”,她一边学习,一边感慨“太累”,还戏言:“人怕出名猪怕壮”,当时还觉得她虽然有些疲惫,但是很“与时俱进”。
2018年4月底,听到照君师母住院的消息。5月4日北大校庆当天,参加完返京同学聚会之后,就匆匆奔赴校医院,在护士的指引下找到师母病床。许师母已不能说话,也已不认识人。我在旁边拉着她的手说些之前去家里的闲话和琐事,师母眼角竟流下泪水,我想她应该是认出我来了。一个多月以后,许师母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因为师母比许先生小几岁,加之性格活泼,总是觉得她很“年轻”,没想到却走在许老前面,让人很是意外和难过。
许先生很健谈,声音又洪亮,但三句不离本行,他最挚爱的莫过于翻译。我因为工作原因,也结识了江枫、屠岸等很多与许先生同辈的翻译家,与他们闲聊,总是能隐约感到老先生之间由于翻译理论而产生的颇多“恩怨”,但又觉得老先生们都很“真”。记得江枫先生翻译的《不够知己》出版时,我正要拜访许府,一时忘记两人在翻译上的不同意见,就带了新书作为“伴手礼”去见许老。许先生翻阅江书,我察颜观色,感到不妙,于是表达歉意,没想到许先生说:“没事儿,我看看他翻的有多差”。我回来后婉转告知江先生,他哈哈一笑说:他也未必翻的多好!
另有一次,熊式一的 《天桥》中译本出版,因为知道熊是许先生的表叔,两人在国外还颇多过从,特意带书去送给许老。没想到书前有一首诗,是同事请屠岸先生翻译的,许老看后颇为不满,还挑出几处他认为译得不好之处给我看,觉得应该由他来译才对。“吐槽”完他又跟我说:屠岸好像90多岁了,你就不要告诉他了,免得让他生气!神情甚是可爱。
许先生对翻译的执着和热爱,使他批评别人不稍假借,别人批评他,他也直言回应,毫不退让。即使年过九十,依然有精力打笔战,斗志高昂。2017年下半年,我看到网上有一位文学副教授撰文说许先生 “英文不过关,还有抄袭嫌疑”云云。我怕许老会拍案而起,未敢告知。哪知第二天,许先生就托师母来电询问某位记者的电话和邮箱,他要撰文回击。我劝他犯不着去回应这些无端指控,但他还是回应了。2019年的11月,我请许老来外研书店做客,当他看到新出的《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马上拿书翻阅,看看是否更正了多年前旧版本中的错别字,足见他的认真,也令我更加明白,许先生是多么爱惜自己的作品及其翻译事业了。
许先生从十八岁开始翻译,到一百岁仍然着迷于翻译,日以继夜,孜孜不倦,译出大量的中外名著,近百部的作品,何止等身?他的精神与毅力,罕见其匹。翻译原是艰巨的工作,不同的语文之间有隔阂,排除隔阂犹如跨越鸿沟,稍不慎会有遗憾。译文要能信、达、雅,知之甚易,行之维艰,三者之间孰轻孰重又争论不休。 许老最重“雅”,也是他与同侪争论的要点,例如他译《红与黑》的最后一句话“她死了”为“魂归离恨天”,引起不小的风波,很多人批评译得不“信”,有违原文的“真面目”;其实,中文读者看到“魂归离恨天”,难道会有 “死了”以外的理解吗?中译能使中文读者“信”、“达”,足矣!将之译成古典的 “魂归离恨天”,提高到“雅”的层次,有什么不好呢?著名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就觉得直译无法沟通不同语法的隔阂,直译貌似“信”,但既不达也不雅,所以主张“意译是王道”。他也特别欣赏许老讲究翻译的三美:意美、音美、形美,有了三美才能将译文提升到艺术的高度,庶几不亚于创作的地位。译诗更难于译文,一般人只能译成“自由体”,但许先生坚持诗要押韵,如章太炎所说,诗不押韵如和尚吃肉,殊不可取。但是要把汉诗译成有韵的洋诗,或将洋诗译成有韵的汉诗,难度都是极高,而许老优为之,连他的老师钱钟书先生都赞叹,许渊冲居然能够“带着脚链跳舞”。
仅举一例,许先生译杜甫有名的登高联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为: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不仅押了韵,而且展示了原句的对仗,也让人深感许老的自负与执着有他的底气!他于2014年获得“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为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不仅是中国第一人,也是亚洲第一人。他的名山之业将如北极光一样,永远不会熄灭!
2020年末,资深编辑胡晓凯女士寄来许渊冲先生 《西南联大新生日记》样书,披览之下,感到兴趣盎然。说来又是缘分,北京外国语大学阿语学院资深教授朱凯先生在我办公室看到本书借去翻阅,发现其父伯章先生竟是许先生大一时的同班同学!而且,许先生当年追求的女神“颜如玉”,竟是伯章先生的同乡好友,两人晚年还颇多通信往来。
于是, 当许先生进入101岁的第一天,我邀请朱教授一同去拜访寿星。朱老师有心,特意回青岛老家找出信件和 “女神”照片,复印后作为礼物送给许先生。许老当天也感到相当的惊喜与兴奋,谈兴甚高,妙语不断。当时我就想写一篇许老日记的读后感, 题目都拟好:《百岁依然一少年》,但迟迟未动笔。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许先生,再知道先生的信息,已是6月17日的噩耗,我匆匆赶去家中,只剩下空荡荡的房间,以及那熟悉的已无人落座的书桌了……
(作者系张家口赤城县人,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为北京外研书店总经理)
2011年3月作者(左一)拜访许渊冲夫妇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表后的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