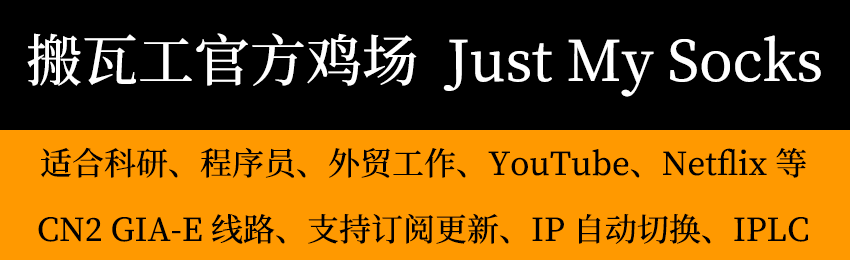
上海芭蕾舞团“云创排”原创芭蕾舞剧《大地之光》
张挺 摄于2022年6月5日
1978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暑假在父亲的供销社玩。父亲的同事中有一个刚从镇上高中毕业的,父亲让我喊他毛结哥。
每天晚餐后,大家聚在后院里摇着芭蕉扇聊天。毛结哥洗好澡,斜躺在竹椅上,对着黄昏的天空,高声唱道:含悲忍泪往前走……这是黄梅戏《天仙配》第三场《路遇》中董永自诉身世的唱段。
毛结哥唱“含悲忍泪”的时候都是带着笑的。他的声音高亢,粗豪,透过院墙,传到远远的河坝上。有一次我在河边看人捕鱼收网,也听到过他的歌声。我的家乡,几乎人人会唱黄梅戏,《天仙配》更是耳熟能详。董永为葬父而卖身为奴,在上工路上“含悲忍泪往前走”,这句唱词音调苍凉,节奏舒缓。毛结哥唱这句时总是蓄足了长长一口气,“悲”字从胸腔里蹦出来,婉转起伏,穿过院子里已经结籽的苦楝树,飘散到院墙外一大片红芋地的上空。我疑心,董永就是在红芋地边遇到七仙女的。
他每天傍晚从开篇的“家住丹阳姓董名永”一直唱到“比翼双飞在人间”。星星亮起来,夜风吹起来,他的歌声才慢慢低下去。
那个暑假,他天天都唱,我以为他这辈子就要在歌声中度过了。
不光唱歌带着笑,他讲话也是永远带着笑的。说完一句话总要呵呵笑两下,好像是征询听者的意见,又好像是对自己刚才说的话不那么肯定。譬如他跟陆国平叔叔说,我们让厨房留一点生猪肝,晚上去钓老鳖,呵呵。不加呵呵,就代表他的决定。加了,则是在问陆叔叔是否愿意去;或者说这只是一个建议,你可以反对。他说呵呵时,眼睛眯起来,全是笑意,脸很圆,也透着光亮。
毛结哥1977年底参加高考,没有录取。那次镇上没有一个人考取。这次高考之后,大家才感到国家政策的变化,有人因而闭门读书,百天不出房门一步,最后考上了重点大学。这人是毛结哥的同学,多年以后,他成了某一领域全国知名的学者。
四年级之前,父亲从不过问我的学业。恢复高考了,父亲才留心我的成绩,给我讲身边各种勤奋学习成才的故事,我却一直为那个百日不出房门的人担忧,他是怎么上厕所的呢?
父亲请毛结哥辅导我的功课。有一天毛结哥布置我做数学课本后面的习题,我一题都不会,他觉得很奇怪,问我,这些没有学过吗?学过了。学过为什么一题都不会呢,呵呵。
我回答不出来,想,这一定是我的错。眼泪就滚出来了,越滚越多。毛结哥说,不会做就不会做,不要哭,呵呵。他开始耐心给我讲题目,不到半小时,我全懂了,都会做了。毛结哥对父亲说,这孩子比我聪明。
每次出差,父亲会给我留十道算术题。他一出门,我最多安生半小时做完一道题,就得跑出去玩一下。院子里有几间大仓库,屋檐下水泥浇筑的散水有几十米长,爬着许多西瓜虫,够我玩半天了。晚上回来写一题,又坐不稳了,喊隔壁同学过来玩,翻箱倒柜,找到了一包生西瓜籽,不能吃,必须炒熟,没有锅,就用铁听装着放在取暖的炭火上烤。听到西瓜籽在铁听里哔卜哔卜地响,还能闻到香气,我早就忘了作业这回事。
玩到很晚,同学要回去了。我收拾残局,想赶紧写作业。可是,拿起笔来,脑袋就歪在桌上了,太困了。
次日父亲回来,先检查作业,才完成两题,就问,很难吗?不难。不难为什么没做完。我无法辩解,低头不语。父亲生气,一顿猛揍。我嗷嗷大哭。打得厉害了,还要去卫生室包扎。毛结哥听到,笑着过来了,要杀伢了吗?呵呵。一边劝父亲,一边安慰我。
我觉得好丢脸。但奇怪的是,这样的事,时常发生,每次情节大同小异。我根本管不住自己的贪玩。毛结哥看到我偷偷玩,就笑着说,不怕打,还是打不怕?
毛结哥跟我讲过他的高中老师,许多是外省市流落到小镇上的有大学问的人,可惜当时学习氛围不好,自己也不懂事,浪费了时光。他还送给我一本厚厚的语文听课笔记。他的字笔画清晰,又大又方,字我都认识,但不解其意,他这本笔记算是明珠投暗了。
除了唱歌,毛结哥还喜欢看杂志。供销社里订了《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安徽文学》。毛结哥和陆国平叔叔看得最多。1980年第9期《安徽文学》上发表的小说《杨花似雪》让大家争论了一个星期。有人认为主人公与遭受太多磨难的前妻杨思萍劫后重逢,一定会与她复合。毛结哥说,不会,小说写的是那个时代给杨思萍造成的悲剧,不是男主人公给女主人公造成的悲剧。他说完了,有点激动,这次他没有呵呵。
我也看过这篇小说,我当然赞同毛结哥的观点,但我一直在想,那些替女主人公杨思萍鸣不平的读者,希望男主人公与她破镜重圆,一定是被她坎坷的命运深深打动了。以至于多年以后学习《复活》,聂赫留朵夫要与被他伤害、沦落到社会底层的玛丝洛娃结婚,老师从宗教救赎的角度展开深入的分析,我的同学听起来一头雾水,我理解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被侮辱被伤害的“杨思萍”的影子。
之后,父亲调到另一个小镇,我考上了师范学校。这当中的几年我没看到毛结哥。重新见到他大概是1983年的暑假,我在父亲单位玩。毛结哥带着妻子,从江城回来,路过小镇,顺便来看看父亲。他妻子身怀六甲,行动已很不方便。我想起他当年唱的《路遇》,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七仙女。我说,没有看到你“路遇”,就看到了“槐荫树下把子交”。现在还唱《天仙配》吗?
唱什么呀,哪有那个闲工夫,呵呵。——他的呵呵,仿佛在否定自己的话,或许有工夫,也不唱了;或许还想唱,但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才几年工夫,我原以为会一直在黄昏唱歌的毛结哥,已经不唱了。我原以为大家聚在一起乘凉的场景会一直延续下去,可不经意间,生活就翻开了新的篇章,有时不知不觉,有时猝不及防。毛结哥看我在写文章,笑着说,学习再不用人监督了嘛。
我正在写一篇散文,题目叫《源》,写我和一个姑娘在秋天的夜晚,沿着弥散浓雾的河边往前走,去寻找河水的源头。姑娘的头发在月光下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
毛结哥看完了,认真地说,女孩子的头发哪里会有什么香味,你嫂子的头上最多是梳头油的味道。
我没有辩解,嫂子也没有辩解,她的脸上是满足和羞赧,还有走了一段路的倦怠。
九十年代后期,乡镇供销社逐步解体。一些职工承包,一些职工单干,一些职工失业。毛结哥在镇上开了一爿小店。日子安定,平淡。
2000年前后,姐姐告诉我,毛结哥得了胰腺癌。那一年他刚四十岁。
那时我已离开家乡,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有时听到他的病情好了,稳定了,我就很高兴。过一段时间,听到转移了,又担心起来。姐姐代替父亲去他家探望,有时见到嫂子脸色铁青,满脸泪痕;姐姐不敢多问,就退回来了。有时,嫂子脸色平静,还有一点笑容;那就是,这段时间平安了。这些年来,嫂子过的全是担惊受怕的日子,在降低又降低的愿望中,忍住泪水,慢慢往前挪动岁月。
八十多岁的父亲说,毛结这样的病,一般人早走了。他能坚持下来,跟他那憨憨的性格有关。他跟人说话从不强迫人什么,都是呵呵地商量着。
这些年来,毛结哥一直在生死边缘游走。他会不会想,高中时期更努力一点或者再躲在房间里复读一年会怎样,供销社不解体或者解体之后他大胆承包会怎样。病痛中回顾往事,他一定想过许多问题。我最想的是,回到那年夏天去吧,回到那些凉风劲吹的傍晚,唱一些幸福欢快的歌谣……
我不知道过了花甲之年的毛结哥如今是什么模样。在我印象里,他还是挺拔的身姿、光润的圆脸,朝着布满彩霞的天空,大声吼着“含悲忍泪往前走”的大哥哥。
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含悲忍泪”是什么意思。
作者:冯 渊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