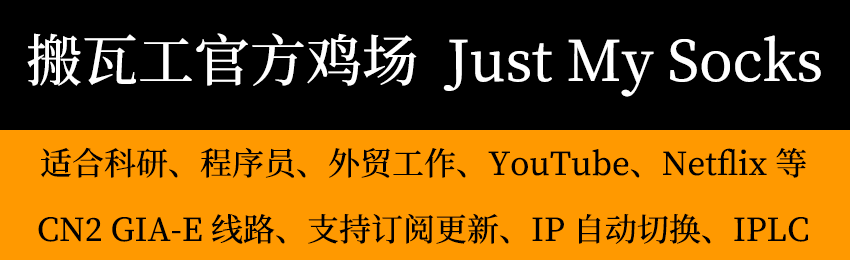
内容提要: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数字技术给电影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全链条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本文认为,数字技术消融了各种媒介之间的特异性,形成一种具有互通性的新媒介语境。在此语境中,电影无论是呈现形态、影像形态、接受形态还是生产形态均表现出“跨界融汇”特征,“看电影”作为一种经典艺术消费方式,正在经历从“观看”到“游戏”的历史性跨越,电影制作者、观众和电影及影院的关系也在进行历史性的重构。
作者简介:张斌,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教授,上海。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0YJC)和上海市哲社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011EXW001)成果。
随着数字技术和媒介形态的迅速变迁,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给电影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全链条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变化。电影已经不能仅仅作为单一的媒介和艺术样态来理解,它处于一种“跨媒介的互动中”,①并且其本身也已经体现了新媒体的种种特征。不断变化的媒介技术带给电影的影响是如此广泛与迅速,以至于英国电影学者罗迪威克(Rodowick,D.N)感叹:“线上和线下的数字艺术和传播持续快速的变化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理解它们的能力。”②的确,今天的电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各种新的电影现象层出不穷,“粉丝电影”“弹幕电影”“综艺电影”“众筹电影”“社交电影”等概念不断翻新,并在媒体报道、艺术评论、学术研究和电影业界激发起热烈的辩论与争论,曾经比较确定的关于“电影是什么”的问题也再一次成为了问题。在新媒体的语境中,电影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是什么?这种变化对电影艺术和产业又有何影响?
本文认为,新媒体语境下电影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是其呈现形态、影像形态、接受形态还是生产形态,均表现出跨界融汇的特征,“看电影”作为一种经典艺术消费方式,正在经历从“观看”到“游戏”的历史性跨越,电影制作者、观众和电影及影院的关系正在进行历史性的重构。当然,这种重构并非完全是“无中生有”,而更可能是“老树新枝”,我们可以在电影的历史起源与发展中找到种种因子。
电影在哪里?从单一银幕到多元屏幕
1964年,加拿大媒介学者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观点。麦克卢汉强调,对媒介内容的关注会让我们忽视对媒介本身特性的观察,因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其他媒介”。这种对媒介技术特性的强调,在电影中也可以观察到,甚至一度成为电影之为电影的基础。电影是一种光影的艺术。如何让光影得到呈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发展的结果,它决定了电影出现在哪里,也决定了影像的存在形态和电影与观众的关系。因此,美国电影学者安妮·弗雷伯格(Anne Friedberg)说:“世界如何被框定(framed)可能和在这个框架中展现的内容同样重要。”③在电影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观影媒介(幕框形式)也发生了数次变迁,而每一次变迁都给电影带来了新的变化。我们可以稍加追溯。
在电影出现之前,已经有众多前电影的原始形态,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爱迪生发明的“电影视镜”(Kinetoscope)。这种装置如同一个盒子,每次只能一个人观看,而且肉眼必须紧靠视镜。这种个体性的亲临接触使观看行为在时空范畴都非常具有局限性,但它也埋下了观众意欲掌控影像的伏笔。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电影投影机将电影视镜中人和影像的直接个体联系变成了一种“非肉体”的群体观看。之后,观众坐到银幕前,而感光胶片记录下的现实世界梦幻般地展现在眼前,引发电影史上有名的“火车进站效应”。从此银幕与电影联系在了一起。汤姆·冈宁认为,“火车进站效应”体现了电影在建立影像奇观的视觉体验上的潜力,构成一种“吸引力电影”。④这种诉诸观众注意力的影像操控在后来的先锋派电影和如今的奇观电影中都可以找到其原初的基因。弗雷伯格从另一个层面讨论这一现象。在她看来,“火车进站效应”与其说是观众震惊于活动影像的“真实效应”,不如说是震惊于影像的“运动效应”,换言之,是运动本身带来了全新的震惊性视觉体验。而这种影像的运动效应强化了观众与银幕之间的两大悖论:影院的物质性与影像的虚拟性(非物质性);影像的运动性与观众的非运动性。⑤这样,观影主体和影像之间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这种隔离,电影也因此发展成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文化工业形态与艺术语言系统。从经典艺术理论来看,这种隔离恰恰是电影成为一种艺术的必要条件。在银幕观视中,观众的视点虽然较之绘画有了变化,但其视点的多元在前述两种悖论的限制下仍是一种假象:观众的物理视点依然单一,心理视点也高度受控。⑥20世纪30年代后期,电视开始出现。作为一种电子传媒,电视的影像呈现方式不同于电影,因此其幕框被称之为“屏幕”(虽然在英文中二者依然使用同一单词screen来表示)。在数字技术和液晶技术出现之前,电视的技术特性在与电影的对比中被不断地放大:屏幕小、清晰度低、实时传播、家庭收视、线性流动(雷蒙德·威廉斯称之为flow)。因此电视更适合信息传递和杂耍娱乐,而在艺术叙事和景观呈现等方面则无法与电影相提并论。电视屏幕的出现虽然也无法解决弗雷伯格提出的观众和视觉幕框之间长期存在的两大悖论,但观众的运动性因为家庭收视环境而得到了部分实现。另外,虽然影像依然与观众隔离,但由于电话和录像设备的存在,电视观众也可以部分掌控甚至介入到电视节目中。⑦
计算机数字技术和网络的发展,给电影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是电影记录载体发生了转变。胶片曾经一度是电影与别的艺术媒介进行区分的主要标志,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这种标志已经不复存在。“胶片怎样成为电影,在哪一点上获得一致认同,并且这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的电影形式的认知,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受到质疑。”⑧数字媒介取代赛璐珞,这标志着电影独特性的技术基石已经不复存在,电影的物质性开始非物质化。数字技术遵循“数值化表述、模块化、自动化处理、易变性和转码”⑨等原则,这种技术同一化显然为电影在生产、存储、传播、播映等诸多方面开启了无限丰富的可能。“电脑技术中的所谓随机记忆(RAM,随机存储器)实际上隐含了对等级制的否定:如果说书籍胶片磁带等以传统方式储存信息的载体是以线性和因果原则为基础的,隐含了传统叙述因素的话,那么,电脑的随机记忆则将数据平面化,将等级结构转化为平面结构。”⑩第二是观影媒介形态得到了拓展。随着液晶显示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屏幕媒体应运而生。电影银幕、电视屏幕、电脑屏幕、手机屏幕、户外公开大屏、可穿戴式设备屏幕等各种或大或小、或固定或移动的屏幕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屏幕的非运动性得到了彻底解放。同时,虽然数码屏幕在物理层面仍然存在幕框界限,但随着“图形用户界面(GUI)”系统被引入其中,从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视觉系统。它在单一屏幕中实现了多个视窗界面的并置,这样,电影一直以来存在的单一固定视点就被打破了,变成了某种具有立体主义性质的多元并置形态的白话“空间”,体现出浅表性、抑制深度以及多层重叠的特点。(11)前述两种变化导致的第三种变化,即是观众与影像之间的关系亲密性。观众通过遥控器、鼠标、键盘、触摸屏、操纵杆、智能眼镜、智能手套以及其他身体器材,在GUI中对图像进行操控、消费乃至生产、传播。
在数字技术的同一性下,媒介之间的技术特性已然消失了,这为长期以来边界泾渭分明的各种影像艺术形态提供了相互渗透、跨界融汇的新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讲,“数字时代,媒介不再是讯息”。(12)
电影怎么样?卧倒的影像与交互屏幕
从单一银幕到多元屏幕的转变,其技术基础是数字技术。电影呈现影像介质的改变从两个方面对影像本身产生了影响。
首先,影像的物理视觉形态发生改变。在原初的电影视镜中,观众透过视镜以一种俯视的方式观看暗盒中的影像,这是一种站立式的居高临下。影像尽管就在观者的眼底并为其所有,但观者既无法在身体上接触影像,也无法在观看中对影像施加任何的控制,是一种孤独的个人游戏。当电影成为真正的大众艺术,看电影成为一种仪式消费活动时,影像从地下升到了高空,吊悬在观众的眼前,观众一般需要仰视才可以观赏电影影像。影院和银幕更大程度地分割开了观众和影像。观众观看电影,更类似于宗教仪式中的膜拜,因此,影像在此时获得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存在一种虽然因机械复制而减弱了的特殊“光韵”。电视被放置在家庭之中,电视屏幕和观众处于等高的位置,影像从空中下到了眼前,观众以一种平视的方式观看电视影像。日常私人空间解放了影像对电视观众的束缚,并且拉近了影像与观众的物理距离,观众可以任意调节与影像之间的距离,影像开始成为家庭中的一员与整个家庭亲密共处。同时,遥控器和录像、存储设备的出现,第一次赋予了观众控制影像的部分权利,不过影像依然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处于观众之外,正所谓“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电脑屏幕以及各种数字视屏的出现,真正打破了屏幕、影像与观众之间的线性逻辑关系,提供了观众与影像之间进行互动的可能。按曼诺维奇的说法,电脑屏幕是一种“交互屏幕”(interactive screen)。(13)数码视屏的交互特质让影像从与观众的站立状态中平躺了下来,以一种卧姿的方式呈现在人的眼下。影像松弛了下来,观众也松弛了下来,影像与观众的关系也从紧绷的线性逻辑中松弛了下来,观众以一种类似阅读小说的方式与平躺的影像进行互动,移动、触摸、选择、删除、传递、评论等等,在生理和心理上与影像达成了高度私密的亲密关系。数码视屏消除了影像与观众之间的物理距离、等级关系和线性结构,回到了观众的手中、怀里、膝上。
其次,影像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德勒兹曾经将影像分成两种类型:“电影1:运动—影像”和“电影2:时间—影像”。他所着眼的是观众和影像之间的感知关系。德勒兹认为,在“电影1”中,运动—影像是一种对世界理性的、稳定的再现,是通过行动来产生反应。这是“二战”前电影的经典模式。而战后“电影2”中的时间—影像则与“电影1”不同,其影像更多地与非理性相联系。沿着这一思路,克里斯汀·达里(Kristen Daly)提出在数字语境下出现了“电影3:交互—影像”。在“电影3”中,电影不再以一种统一的、不变的艺术形式存在,而是参与到跨媒介互动的世界中,是一种用者的电影(cinema of user)。(14)达里的观点与罗德威克的看法相互呼应。罗德威克在谈到数字影像的特点时说,“观众不再被动地屈从于影像中那不可逆转的时间流中,而是在看与读之间变化:一边沉浸于观看一边热衷于操控,两者处于一种相互交叠的状态”。(15)因此,数字电影中的互动影像具有德勒兹和加塔里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2:千高原》一书中提到的块茎状特点,遵循异质联系、多元并置、非示意性裂变、绘图与拼贴等原则,即遵循的是非线性的数字逻辑。(16)正是这种影像本质的转变,让电影向世界敞开了一度关闭的怀抱,新媒体语境下电影的生产和接受形态正在发生的重构,本质上是影像与人关系的重构。
电影如何看?主动的观众与游戏接受
汤姆·冈宁在《吸引力电影》一文的结尾以一种深具历史意味的文字谈到,“电影史上的每一个变化都意味着它对观众的影响方式的变化,每一个时期的电影也都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建构它的观众”。(17)的确,新媒体语境的存在正在重新定义电影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上,电影是一种以供观赏的叙事艺术,具有封闭的文本特性。因此,电影的消费者只能是“观众”,影像之于观众,犹如镜中花、水中月,唾手而不可得,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但在数字媒体语境下,观众不再是“观者”(viewer),而变成了“游戏者”(player),入乎内而出乎外,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电影本身也从一个封闭的文本变成了观众永不停歇的游戏实践,电影的交往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种游戏接受主要体现在:
第一,时空上影随人动。多元屏幕的出现诞生了各种各样的屏幕媒体。它们不但在物理样式上多元,而且在屏幕内部亦具有多元幕窗的功能。如前所述,这些屏幕媒体消解了影院的物质性与影像的虚拟性,以及影像的运动性与观众的非运动性之间的悖论性障碍。电影从黑暗的影院走了出来,走到人们每时每刻每地都能看电影的屏幕上。(18)从这个角度讲,影院无处不在,运动无处不在。电影成为时刻陪伴我们左右的一个游戏,参与了我们的生活。移动的观众与虚拟的影院共同构成了新媒体语境下电影观视的主要状态。今天,地铁等公共交通中的“低头族”、城市公共空间大屏幕前的“抬头党”就是这种状态的形象写照。
第二,手段上搜索导航。可操控的数码视屏和块茎状的互动影像为电影观众提供了无穷的可选择性和可处理性。因为,“在数字复制时代,作品的价值不再是膜拜价值和展示价值,而是操控价值”。(19)电影不再是被推送到观众眼前的被动展示,而是观众主动搜索导航的结果,是在茫茫的数字影像海洋地图中将电影“拉”出来。通过搜索引擎和导航设置,观众在各种视频网站和电影下载资源网站的超量数据库爬梳,犹如在漫长的游戏征途中寻找宝物。另外,互动影像具有维基百科的数字基因,它赋予并接受观众对于文本的访问、压缩、补充、删除、重构等各种行为。这种可处理性是操控价值的高度体现。在技术上,很多视频网站都有可以提供让观众自主处理视频影像的能力。观众通过对素材的重新剪辑,甚至是对原始素材中不同机位、景别的选择,形成一部新的作品。2012年,周迅、井柏然主演的I Know U在国内首开这种全开放式电影的先河。电影的单一文本性被打破,变成了一种如约翰·菲斯克所言的“生产者式文本”。
第三,心理上群乐众欢。数码视屏的个人化并没有带来电影交往功能的下降,相反,由于社交网络和通讯手段的高度泛在化和实时在线性,新媒体语境下电影的交往功能随着“游戏者”之间的频密聚集和连接呈现前所未有的膨胀。传统电影固然亦有交往功能,比如曾经一度流行的“坝坝电影”就具有这种交往功能,但随着观影模式的影院化,这种交往功能随之终结。另外,人们看电影后也大多会谈论电影,并撰写评论在媒体上发表传播,这也是一种交往。但这种互动的规模及效应总是滞后并且无法及时反馈。数字媒体的开放性、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给观众互动留下了巨大空间。观众在豆瓣、时光网、微博、朋友圈等写评论,点赞、评分,相互交流扩散电影。作为“游戏者”,观众全情投入忘我参与,在此过程中获得认同和情感的满足。另外,数字媒体放大了粉丝群体集聚和行动的能力,具有互联网基因的“网生代”电影观众造就了以《小时代》系列为标志的叫座不叫好的粉丝电影。另外,弹幕电影这种形态,直接将社交功能融汇到电影文本的再生产里。当屏幕上“吐槽”如弹雨般而过时,游戏者在这种万众齐欢中的快乐与游戏(电影)本身合二为一了,犹如升级了的“坝坝电影”。
电影从何来?多向融汇与跨界生产
在记录载体数字化、影像本质互动化、观影媒介多屏化、接受空间日常化等情景下,电影这一概念与产业活动出现了“泛化”。“近一个世纪建立起来的电影常规不断被突破、原本稳定的电影边界不断扩展,结果导致电影定位不断更新,有些激进的学者甚至将任何包含活动图像的艺术形式都视为电影。”(20)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自然应该有其基本的艺术规范,但这种规范在今天数字媒介的语境下也的确在发生变化,正在进行历史性的重构。这种重构体现在电影生产上,就是广泛而频繁的“跨界融汇”现象。
首先是生产者的跨界。电影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艺术生产活动,涉及到大量专业工种和人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编导摄录美服化等。如今数字技术以0和1的代码统一并大大简化了电影生产的专业门槛,为电影从前期拍摄到后期传播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时促进了自我生产(DIY)、作品共享、开放软件源代码等开放式生产的大规模出现。以此为背景,许多电影圈外的人开始大量进入电影的创作生产,传统的专业与业余的分工被打破。一方面,传统的文字工作者开始进入电影生产领域,利用其文字作品建立的庞大粉丝群体和期待视野迅速取得传统电影生产无法想象的市场成绩。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韩寒的《后会无期》即是如此。另一方面,由于数字技术、便携式摄录设备以及影视网络数据库的支撑,大量网络用户开始投入到电影视频的生产中,当前方兴未艾的微电影浪潮就是明证。有些优秀的微电影,如《老男孩》等,在前期网络点击聚集海量跟追观众之后,再被拍摄成大银幕电影到院线放映,利用其超高网络人气获得院线高票房。电影封闭的工业生产链条正在被众多由外入内的闯入者所打开。最后,电影的投资来源也开始平面化和多元化。互联网金融经济形态的出现,让电影投资从大制片方的单独和联合投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开始向“众筹”的方向发展。阿里巴巴的余额宝中的娱乐宝就是电影“众筹”的一种方式。《天将雄狮》《狼图腾》《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十多部影片就有这类募集资金。同时这种众筹通过探班、与明星见面等权益活动,赋予部分投资者(观众)以参与电影生产的机会,将观众后期观看的单一消费行为融汇进电影生产链条的更丰富复杂的互动交往中。
其次是艺术形态的跨界。自从莱辛的《拉奥孔》发表之后,媒介介质的差异便构成艺术形态的核心标志。曾几何时,我们还在绞尽脑汁研究电影和电视这两种媒介和艺术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差异,今天数字化已经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消解了电影、电视以及其他影像艺术媒介介质之间的主要差异,从而为艺术形态之间的融汇互通打开了大门。但这种跨界其实并非没有原始的根源。正如前文所述,在电视发明的初期,电影和电视之间的互通就存在,不过那是一种原初的可能,而不是一种自觉的追求。今天,电影与其他影像艺术形态之间具有更强烈、自觉和广泛的融汇。这种艺术形态的融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电影与视频艺术的融汇。数字技术导致数码摄录设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规模进入市场,视频第一次成为普通人可以生产的东西,非线性编辑技术和软件的广泛运用则让视频艺术成为现实。而互联网的发展为视频艺术提供了存储、传播与重写的平台。数字媒体“鼓励交叉与混合化,从而创造出新的语言并重新定义了艺术的性质”。(21)这种被曼诺维奇称之为“DV现实主义”的视频艺术推动了电影的视频化发展。
2.电影与电视的融汇。看电影和看电视曾经是两种具有明显差异性的艺术消费活动。要说两者之间的关系,最主要还是体现在电影作为电视的传播内容而存在,“电视电影”就是这种状态最好的表述,但我们几乎没有在电影中接受电视节目的体验。今天,不但电影和电视剧之间的相互转换成为常态,如近几年每年春节档都会放映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动画大电影。而且电影和电视节目之间的互通也成为了现实,近来被热烈讨论的“综艺电影”就是如此。《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在电视节目播出之后快速制作完成的电影在影院也获得很高的票房。这突出体现了电影的交往功能,因为在这些电影中,故事早就是观众熟知的内容,也非关注的焦点,而看电影本身,也就是游戏本身,这才是重点。
3.电影与电子游戏的融汇。电影和电子游戏的融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电子游戏作为题材进入到电影中。《古墓丽影》《生化危机》《波斯王子》《寂静岭》《拳皇》等一大批电子游戏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另一方面,电影授权对电影自身进行游戏开发,如《指环王》。同时,电影和游戏在产业营销上也互相融合。游戏借助预告片、资料片等来进行推广司空见惯,而电影影像和叙事结构的游戏化也是非常明显的现象。正如列昂·葛瑞威奇所说,好莱坞电影的“视听形式日益呈现电脑生成趋势,而新兴的全球游戏业也越来越亲近照相写实美学,这反过来又对其叙事形式的性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2)
4.电影与虚拟现实的融汇。传统电影是一种封闭的线性叙事,而虚拟现实则是一种参与探索式的开放并置结构。但电影和虚拟现实都是对现实的替代乃至是超越,是对后现代哲学家鲍德里亚“虚拟现实比现实更真实,仿像就是现实”断言的具体写照。正是因为这种替代需要或仿真特性,可以将虚拟现实视为电影这种媒介形式的自然进化。《黑客帝国》《阿凡达》《哈利·波特》《魔戒》等电影正是对这种虚拟现实的吸纳。而虚拟现实也借助于智能移动终端的摄录设备和动作表情影像捕捉设备,通过网络连接自主添加和生成影像来建立虚拟现实。比如谷歌的全景地图、都市街头的大屏幕影像互动装置、谷歌眼镜等可穿戴智能影像设备等。
再次是美学趣味的跨界。电影曾经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文化工业的核心,这种高度垄断和封闭的文化产业所灌注和传达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美学趣味,是一种社会等级秩序的再生产。而新媒体环境下的电影正在变成达文波特所说的“元电影”。这种元电影“放弃了单一固定银幕或屏幕,越来越多地将自身投射于日常环境,因此变成了让人们从事发现活动的即兴性学习伴侣。换言之,它正朝即兴电影发展”。(23)这是大众展现自己美学趣味和需求的新兴手段和平台,是对于传统电影美学趣味垄断的反抗。大众依托数字技术和网络支持,一方面对传统的经典电影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和重新编写,对电影权威进行解构,张扬自己的美学趣味和价值批判,当年胡戈那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可以视为代表;另一方面,电影也大量吸纳大众所传达或喜欢的美学趣味并与之融汇对话,周星驰的系列作品可以视为代表。同时,当下电影中出现的所谓“美学粗鄙化”现象也与此不无关系。而大数据的出现,更为电影生产精确捕捉大众的美学趣味提供了技术手段。数字美学、数据美学和传统电影美学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消解。
1946年,安德烈·巴赞为《评论》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完整电影”的神话》。巴赞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电影诞生的原动力并非是科学技术发明的结果,而是人类意欲再现世界原貌这一共同的念头。这一共同念头被他称之为完整的现实主义神话,而从这一神话中诞生的电影,则被他称为“完整电影”的神话。从这一视角出发,巴赞指出:“貌似悖论的理由是,一切使电影臻于完美的做法都不过是使电影接近它的起源。电影确实还没有发明出来呢!”(24)在近七十年后的今天,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巴赞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置身于被称为“新媒体”的语境中,不再只是在银幕上需要仰视的运动画面与梦幻奇观,共存在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体现出从“观看”到“游戏”的转变。我们可以说,当下电影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能够接近于实现“完整电影”的神话。
注释:
①电影这种跨媒介的互动,被高蒂尔描述为处于“电视革命和数字革命”的夹缝中,参见Philippe Gauthier(2014),What will film studies be? Film caught between the television revolution and the digital revolution,New Review of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es,Vol.12,No.3:pp.229 233。
②Rodowick,D.N(2008).Dr.Strange Media,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Film Theory.In Inventing Film Studies,edited by Lee Grieveson and HaideeWasson,pp.374 397.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③Anne Friedberg(2009).The Virtual Window:From Alberti to Microsoft,p.2,Cambridge,Mass:MIT Press.
④[美]汤姆·冈宁《吸引力电影:早期电影及其观众与先锋派》,范倍译,《世界电影》2009年第2期。
⑤(11)同③,第155页。
⑥根据劳拉·穆尔维的研究,经典好莱坞电影的视点由“窥淫”和“认同”构成,观众在观影时的视点被强迫统一到角色、摄影机和拍摄者的视点中。参见Laura Mulvey(1975).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Screen 16.3 Autumn 1975,pp.6—18。
⑦这种对差异性的强调让我们忽略了早期电视与电影之间曾经存在的相互关系。据William Uricchio的研究,早期电视和电影在技术上存在互通。比如1935—1938年德国采用Fernseh AG公司基于电影技术的电视系统传播新闻时事和电影,因为这种系统在当时比RCA公司的全电子电视稳定得多。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Fernseh用胶片拍摄体育比赛,在现场用磁盘/图像解析器扫描处理并当场传送到电视收看。Fernseh的电视系统还能将电视图像转化到电影胶片上,并且很快处理并现场放映。另外,电影和电视在产业上也有交叠。比如派拉蒙公司1938年拥有杜芒电视公司一半的股份,拥有美国第一批九个电视台中的四个。制片厂还将电视直接引入到电影中,形成一种所谓的“影院电视”(theater television),并于20世纪50年代探索在电视上订购和付费点播电影的方案。参见William Uricchio(2014).Film,Cinema,Television…Media? New Review of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es,12:3,pp.270-271。同时,早期电视的收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公共空间中的集体收视,如纳粹德国就曾经在公开场所设置了四百个左右的电视收看点,用来向公众传达重要信息。这已经展现出屏幕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中的双重可能,展现了屏幕横跨两种空间的原始潜能。参见Urrichio,W.(1989)Rituals of Reception,Patterns of Neglect:Nazi Television and its Postwar Representation,Wide Angle 11(1):pp.48 66。
⑧Janet Harbord(2007).The Evolution of Film:Rethinking film studies,Cambridge,Mass:Polity Press,p.5.
⑨Lev Manovich(2002),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Cambridge,Mass:MIT Press,p.49.
⑩孙绍谊《电影经纬:影像空间与文化全球主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页。
(12)Nicolas Negroponte(1995).Being Digital,New York:Alfred Knopf,p.71.
(14)Kristen Daly.Cinema 3.0:The Interactive-Image,Cinema Journal,Vol.50,No.1(Fall 2010),p.82.
(15)David N.Rodowic(2007).The Virtual Life of Fil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177.
(16)刘景福、黄奋鸣《平躺的影像:新媒体语境中的电影艺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19页。
(17)同④。
(18)屏幕媒体充斥我们的生活,构成了新的视觉传播模式,打通了内外、前后、左右,形成了屏幕媒体无缝全覆盖的现状。参见苏状、马凌《屏幕媒体视觉传播变革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19)[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20)黄鸣奋《泛电影:21世纪初的媒体与艺术》,《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21)Francesco Bernardelli(2008),From Film to Video Art,In Vertigo:A Century of Multimedia Art from Futurism to the Web.Edited by Germano Celant,Skira:Museod Arte Modemadi Bologna,pp.297-306.
(22)[新西兰]列昂·葛瑞威奇:《互动电影:数字吸引力时代的影像术和“游戏效应”》,孙绍谊译,载孙绍谊、郑涵主编《新媒体与文化转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43页。
(23)Glorianna Davenport(2003).Interactive Cinema Group,MIT Media Lab,In Future Cinema:The Cinematic Imaginary after Film,Edited by Jeffrey Shaw and Peter Weibel,Cambridge,MA:London:MIT,pp.279.转引自黄鸣奋《屏幕美学:从过去到未来》,《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24)[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