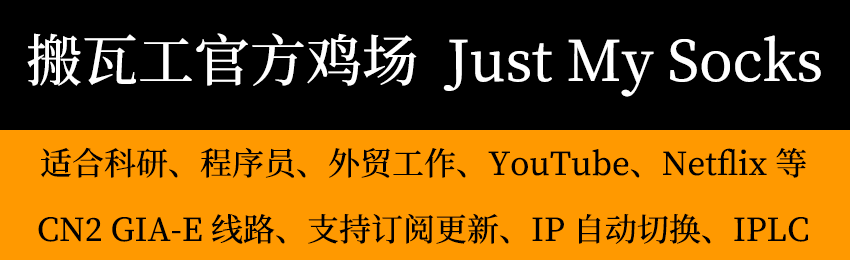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一词涵义相对简单,一般不作他用,主要是指“国家”,专指中国之全部领土,具有地域、文化、政治、民族上的特定涵义。古代的“中国”一词,其涵义则较为复杂,且前后发展演变特性十分明显。
地域意义上的中国
地域意义上的中国,是指中心区域,即“天下之中”,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涵义相近。古代华夏族群活动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为是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最初主要是指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的区域,后来随着华夏族群、汉族群活动范围的扩大,黄河流域乃至更广泛的区域被称作“中国”。
西周文献有明确的地域意义上的“中国”观念。如《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里是说,上天既然已经把“中国”的臣民和疆域赐予周先王,当今的周王只有施行德政,教导殷顽民,使其心悦诚服,以此完成先王所承受的大命。
这里的“中国”特指一定的区域,应为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区。汉代以后文献常见地域意义上的“中国”,其范围有所扩大。如《史记▪天官书》:“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此“六国”当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等诸国区域。《晋书▪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此“中国”显然是指三国时期的魏国版图。
都城意义上的中国
都城意义上的中国,是国家政治中心的别称,专指都城、都邑、京师。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毛传》:“中国,京师也。”这里的“中国”与“京师”涵义相同,特指周王朝的都城。
东周文献常见以“中国”代表都城的记载。如《孟子▪万章上》:“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孙爽《疏》:“所谓中国,刘熙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里是说舜到帝尧之都——“中国”继承“天子”之位。
又如《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是说齐王想在国都之中给孟子单独建一个馆所,送万钟的粮米来供养他的弟子。
再如《国语▪吴语》记载越国在分析吴王夫差必败时说:“吴之边鄙远者,罢而未至,吴王将耻不战,必不须至之会也,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韦昭注:“中国,国都。”这里是说吴国必然会以国都中的兵力与越国作战。
族群文明意义上的中国
族群文明意义上的中国,即天下文明的中心。因古代华夏族群和后来的汉族多建都于黄河流域,政治优越,经济、文化发达,文明化程度远超于周围四边之地,是四方仿效的榜样,故称其所在地为“中国”,以对应周边地区的“四夷”。
如《战国策▪赵策二》:“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这里的“中国”主要是指东周时期中原各诸侯国,部分等同于“华夏”“中原”之涵义。西汉司马迁《史记》在记载中原诸侯与秦国、吴国交往时,也往往用“中国”一词,如《秦本纪》:“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汉代以后“中国”一词也泛指中原各族群居地。
国家意义上的中国
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专指中国境内尤其是黄河流域建立的单一的国家。如《汉书?陆贾传》:“皇帝(刘邦)……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汉帝国,表示汉王朝有效统治的整个区域,自称“中国”。
明清时期,在对外交往中,也常常自称“中国”。如《明史?外国七》:“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以“中国”为正式国名。只是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中国”才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当今“中国”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即同时并存的多支考古学文化联系密切,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被认定是“最初的中国”或“早期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当多的学者认识到黄河流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区域,早在史前时期该区域就以核心作用和影响力将各地维系为一个整体。
如1968年张光直先生认为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文化,由于彼此影响和碰撞相互连接组成一个更大的“相互作用圈”,这个作用圈形成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核心。到了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模式,认为史前文化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格局。
近些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以考古学材料直接认定“最初的中国”。如韩建业先生认为先秦时期存在一个“早期中国文化圈”,早期中国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前后,正式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在庙底沟时代,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迅速发展,文化的扩展自然形成三个层次的圈层结构,标志着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
此外,李新伟先生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300年左右,“也就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红山文化中晚期、崧泽文化中晚期和凌家滩遗存时期”,各种史前文化交相辉映,建立起远距离的“社会上层交流网”,逐步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圈”,“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五种涵义基础上的“最早的中国”
古代有关“中国”一词的涵义较为复杂,且具有发展演变特性,主要有地域、都城、国家、华夏族群文明等四种涵义,当今学界又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认定某一文化圈具有“中国”的属性。学界有关何为“最早的中国”之争议,是建立在这五种“中国”涵义基础上的、不同学者的不同认识或解读。
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的标准,须满足三项基本条件,即地理范围上局限于黄河流域,社会形态须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包括邦国和王国)以后,文化发展占优势地位。符合这三项基本条件下的不同涵义上“最早的中国”,时间上大约为龙山时期到汉代之间,空间上主要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广义中原区域。
目前明确记载、较为可信的地域意义上“最早的中国”主要是指西周初期的伊洛地区(今洛阳一带),也泛指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区;都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周时期的洛邑等都城;族群文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应为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华夏诸侯分布区;而国家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大约是在西汉帝国以后。
从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指向龙山时期的陶寺文明最有说服力,其应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在认同存在夏王朝、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前提下,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无疑算作是“最早的王国”,也应是当时的“中国”,但不属于“最早的中国”。
责任编辑:普庆玲 PSY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