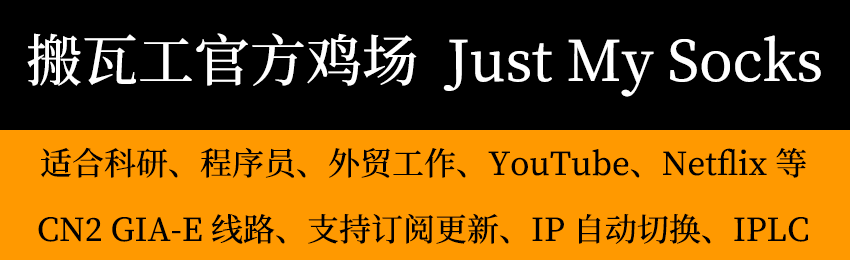
按:正在撰写一本以徐震为研究对象的关于当代艺术与传播学的论著,奈何琐事缠身,始终拖延。眼看原计划8-10万字内容的完稿日遥遥无期,为敦促自己尽快写作,故而将全书的第一章“挪用:徐震的艺术描红簿”里五个小节的第一版草稿以不定期连载的方式在此发布。内容分别是“造作,或博伊斯的死兔子”、“恶搞,或杜尚的蒙娜丽莎”、“性化,或杰夫·昆斯的色情”、“奇观,或达明·赫斯特的鲨鱼”,以及“商业,或安迪·沃霍尔的工厂”。
安迪·沃霍尔
近年来,纵使在艺术品二级市场的国际舞台,频频上演天价拍卖的骇人新闻,然而即便是一幅成交价高达10亿人民币的极品,也不足以掩盖这样的事实:无论艺术品的价格企及怎样的高度,当前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艺术生产方式依旧滞留在小农经济时代。这不啻于以事实为依据,向经典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坚实的反驳——生产方式的落后与商品交换价值的高涨竟可毫无冲突地共存。依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方式乃是社会生活中人们谋得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料的方式,以及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关系。它可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大范畴。就生产力系统而言,当代艺术产业的生产者主要是以个人形式工作的艺术家;绝大多数的生产工具仍是依靠人力操纵的石木与金属工具,而非大规模劳动力通过动力机械、自动化机械等现代化设备;生产对象则是把未经加工的自然物和已然成为人造物的东西经艺术加工后成为艺术品。不难发现,它违背了马克思对于生产工具奠定社会性质的判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在当代艺术同样挤进全球资本主义流通渠道的当下,绝大多数艺术家仍在使用“手推磨”转动他们名利双收的命运之轮。不妨再看生产关系,如今掌握着艺术生产资料的画廊主俨然是占据着一亩三分地的地主;他们所合作的艺术家则堪比佃农(独立艺术家或许可算是自耕农),把生产出的商品交付给地主进行销售,一旦销售成功后便对半分账。在这种生产关系下,艺术博览会与拍卖会这类定期举办的密集型销售市场,恰似农业时代的庙会。地主的一手产品和顾客的二手产品被纷纷陈列在此,等待着赶集而来的顾客按需选购。总之,不论当代艺术在市场上创造的产值多大,它囿于生产方式上的落后,总是显得产量与产能有限,并且始终拘泥于小农时代的经济体规模。
沃霍尔机械复制的时尚符号——玛丽莲·梦露
历史上,艺术家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类似手工作坊性质的工作室,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从乔托、提香再到伦勃朗,乃至后世的著名艺术家,他们都经历过为前辈艺术家代笔的“学徒期”,也享受过广收门徒代为捉刀,最后如同一代宗师般在作品上贴牌式签署自己名字的殊荣。但是,真正被冠以“工厂”之名,步入流水线批量生产的大工业时代生产方式,直到20世纪中叶才由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开始——令人惊讶的是,它居然比工业革命整整迟来了多达两个世纪,比福特(Henry Ford)采用流水线从事生产则晚了半个世纪。可是,即便姗姗来迟,沃霍尔依然是凭借着艺术生产方式上的革新足以被载入史册之人。相似于1908年工业流水线上诞生了福特轿车,而被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里把这一年戏称为“福特元年”,1963年也足以被命名为艺术领域工业生产化的“沃霍尔元年”。是年,沃霍尔在纽约租下了工作室,采用颇具未来主义风格的装潢方式,内部充斥着大量的银色锡箔纸和银色油漆,最后将其命名为“银色工厂”。有别于传统艺术家工作室的手工作坊属性,仿照工业生产线来量产作品的沃霍尔工作室名副其实的是“工厂”。在这里,被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批判为致使艺术品“灵晕”(aura)丧尽的机械复制大行其道,按照商业订单的多寡,批量炮制着丝网印刷版画。不仅如此,在艺术生产工业化之外,沃霍尔还是最早涉足艺术工业与流行时尚跨界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工厂”绝不只是为产业工人提供工作岗位那么简单而已,它同时也被塑造为时尚名流的聚集地,众多艺术家、畅销文学作者、电影明星、摇滚歌手乃至社会名流等时髦人物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把“工厂”塑造成了纽约最为时尚的派对欢场与沙龙圣殿。
八十年代沃霍尔在天安门城楼前的留影纪念
随着沃霍尔被嬉皮士与雅皮士们奉为艺术偶像,继而渗透至整个视觉文化领域,他的工业化生产方式逐渐成为全球众多艺术家竞相标举的艺术时尚最高纲领。1982年,沃霍尔远渡重洋,展开了他的中国之旅。同年,另一位波普艺术家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来华,并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安徽泾县宣纸厂里古老的手工造纸技艺,又于三年后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了展览。这些当时为数不多的重要艺术事件,在刚刚学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艺术界掀起了“波普旋风”。其中,沃霍尔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它不仅在艺术的美学趣味上提供了一份当代西方时髦文化的图像清单,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探究到了他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奥秘。如果把沃霍尔的商品图像和生产方式一分为二看,那么在中国,王广义等人随即就通过“政治波普”改造出了极具政治意味的汉化版波普艺术。但是,真正承袭了沃霍尔生产方式的中国艺术家,则要延宕到本世纪初才得以诞生——2009年,徐震创立了“没顶公司”(MadeIn Company),开启了极具商业意味的汉化版“银色工厂”的大门。
2014年时没顶公司的“全家福”照片
在没顶公司之前,中国尚无真正意义上由艺术家通过企业化管理与运营,从而建立起致力于创作、传播以及项目策划和执行的商业艺术机构。通过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艺术商品的资本化,徐震绝不只是简单地解决了提高商品产量与拓展流通渠道等初步需求而已。在更深远的层面上,他借此把作为艺术家和企业主的自己嵌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等诸多体系之中,模仿着沃霍尔的成功步伐,踏上了沃霍尔的未竟之途。除了雇佣大量艺术产业工人,分工化地从事不同的艺术商品的生产,以此提升生产的效率与规模,继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创立没顶公司的革命性意义,首先来自于它打破了艺术领域传统生产关系的稳定性。公司尚无之时,徐震与他长期合作的上海香格纳画廊与北京长征空间之间的关系仍是“佃农-地主”模式。那么,公司的成立就意味着双方达成了崭新的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其商业本质也就被改写成了:作为生产商的没顶公司与作为经销商的香格纳画廊与长征空间之间的产业链匹配。同时,此举形成的连带效应也表明,在没顶公司内部艺术家徐震和实际制作作品的雇工之间的关系,也从原先的农业社会“佃农-二级佃农”模式晋级为工业社会“资本家-工人”模式。较之于这些实际层面的改观,被艺术领域戏称为“没老板”的没顶公司创始人徐震,他在2009年前后的名分差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仅有的改变无非是他在合作画廊的可销售作品名录上的创作者署名,从“徐震”变成了他的笔名“徐震-没顶公司出品”,而这根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实际改变。
没顶画廊展览海报
2012年年末,著名的“马王赌约”惊动了中国商界。在CCTV经济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马云与王健林就“电商能否取代传统的店铺经营”展开激辩,并豪言投入一亿元人民币作为赌注,下注电商可以在2020年前占有中国零售市场份额的50%。从此,“渠道为王”甚嚣尘上,“产品为王”喑哑失色。或许,也正是在这种全社会都沉浸在崭新商业思潮震荡的氛围之下,没顶公司才于2014年创办了旗下的子品牌“没顶画廊”。值此,徐震不愿仅仅在艺术市场上充当生产商的角色,他的商业版图逐步染指经销商的功能。如此一来,他也变相地抬升了没顶公司在产业结构上地位——它旗下初创不久同样代理徐震作品的没顶画廊,在层级上与他的另两个中国老牌艺术经销商香格纳画廊与长征空间平起平坐;那么没顶公司作为没顶画廊的母公司,自然跃居在香格纳与长征的辈分之上。另一方面,如果说香格纳与长征垄断了绝大多数行销海外的成名艺术家的作品,那么没顶画廊因“同辈”的名分,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分庭抗礼。只不过,前者囤积居奇了大量优质的稀缺商品,一时难以撼动其占有的市场份额。故而,没顶画廊基于资历和财力有限的实际情况,目前只能把艺术家的作品视为期货,积极地在它们未来的增值空间上进行投资。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众多在后文革时代出生的优秀年轻艺术家,在近年来都与没顶画廊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合作。
没顶公司旗下“徐震品牌”的Logo
值得注意的是,没顶画廊并非没顶公司推出的首个子品牌。2013年,徐震为了打造个人IP在公司旗下孕育了“徐震品牌”的诞生。这种“自孕自产”的举动(徐震创办了没顶公司,而公司又成立了“徐震品牌”)再度实现了一次更迭“笔名”的署名游戏——才用了不久的“徐震-没顶公司出品”旋即被“徐震®-没顶公司出品”所替代。这也从侧面暗示着,徐震、没顶公司与徐震品牌并无本质差异。虽然如此,但是表面上的文字游戏却暗含了他在不同商业模式下寻求必先正乎名的营销策略。当然,假如只是把它看作是爆米花更名哈力克,冰淇淋改称吉拉托这些用发音缠绵、引发异域幻想的高端化洋名来抬升售价,就未免太目光短浅了。徐震的更名风波远非商业上通过货品名称时髦化来增长价格的伎俩所能比拟。只消对它进行简单的梳理,就不难透析出它与整个时代的商业生产乃至消费升级保持同步的身影。倘若把艺术家徐震本人视为前现代生产方式的佃农,那么没顶公司则相当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工厂,至于徐震品牌显然就是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旨在占据用户心智的品牌化营销的个人IP。
左为徐震专卖店,右为没顶画廊
早在徐震品牌诞生之前,徐震本人就已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具有相当的知名度了。因此,只经历短短三年的“IP孵化期”,他就适时地调整了商业战略的重心,按部就班地驶入“IP变现期”。2016年11月,他在上海西岸地区开设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徐震专卖店”,作为“徐震品牌”的子业务,它位于跟“徐震品牌”平级的“没顶画廊”之侧。与其说,它们是比邻而居的一家母公司旗下的两个子品牌项目;毋宁说它本质上就是把一个门店分而治之的两个柜台——当没顶画廊经销着其他艺术家商品,赚取代理费利润之时;徐震专卖店仅仅只是直销他本人的产品,无需与人分利,就可独占全额销售利润。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而言,徐震专卖店的横空出世或许意味着填补了艺术商业的某种结构性功能缺失。毕竟,此前的画廊销售模式总是扭捏作态于不愿承认艺术品的商品本质(哪怕在实际销售过程中,它们从未缺失任何商业利益),也刻意地标榜着艺术品和艺术衍生品存在着天壤之别的差异。但是,徐震专卖店却直言不讳地认可了那里所有的艺术品都是商品,敬请所有人以对待商品的方式来看待艺术品,并用在商业上消费的方式去在美学上感受艺术。同时,它也打破了艺术品与艺术衍生品之间被人为设置的观念壁垒。在那里,一切都没有分别,所有的物件都只是被作为商品而等量齐观。这种基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进程的作用,或许至多徒有历史重要节点上那些惯见的纪念意义,但是对于徐震本人而言,它所奠定的能够获取实利的商业模式就显得意义非凡了——从独自劳作的自耕农(早期从业时并没有画廊合作),到为两家大地主分别劳作的高产佃农(随后香格纳画廊与长征空间分别代理了他的部分作品),随后摇身一变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的工厂主(创办了没顶公司),再到如今业务实现了囊括整条艺术生产产业链(没顶公司用于生产,没顶画廊用于销售,徐震品牌作为IP,徐震专卖店则致力于营销)。至此,徐震真正地完成了从白手起家到缔造艺术商业“托拉斯帝国”的壮举。
第一版草稿,2018年1月
第一章“挪用:徐震的艺术描红簿”终结。连载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