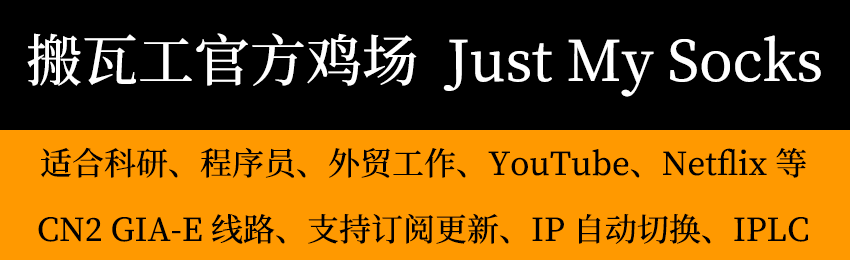
出于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机器视觉作为新的权利工具需要被了解、研究,如同从古至今所有的政治工具:法律、警察、学术、道德体系。在被图像看到的被动中我们认识到数字化图像具有社会调节作用,一种总在脱离民众,汇入权力上游,最终致使已有权力手段更加精准的社会功效。通过对数字化图像的商业应用的研究,本文从手机摄影的算法技术与社交媒体中的代理入手,讨论了在信息爆炸的当下如何区分信息与噪音,究竟是谁在区分?谁才是我们每个社交网络使用者表达的主体?
©Brown University
代理政治:信号与噪音
作者:Hito Steyerl
译者:吕芃
前阵子我去见了一位非常有趣的软件开发师,他正在研发智能手机科技。传统上认为摄影就是在理想情况通过一个索引链接(indexical link),利用科技手段去呈现现有的东西。但情况还是这样吗?这位开发师向我解释道,现代智能手机的相机所用的技术和传统相机非常不同,它们的镜头基本上又小又糟,这也就意味着手机相机的传感器所捕捉到的将近一半数据都是噪点。解决这个问题的诡计其实是编写一种能清除噪点的算法,或者是能从噪点中分辨图片的算法。
那么相机如何知道它该怎么做呢?很简单,通过扫描你的手机或你的社交媒体网络中所有的照片,包括你的联络人。它分析那些你拍下的,或与你相关的照片,并尝试匹配照片中的面部和形状,最终把它们与你联系起来。通过对比你和你的社交网曾经拍摄的照片,算法会猜测你现在想拍什么。它创造的现有图片是基于储存库中早先的图片。这种全新的模式叫做运算摄影(Computational Photography)。
一位学者为了说明运算摄影而做的示例图,图为多伦多大学的Hart House,结合了HDR和全景拼贴技术。
©Wikipedia
运算摄影或许会拍出根本不曾存在,但算法认为你乐意看到的东西。这种类型的摄影是带有推测机制的,相关的(speculative and relational)。它是一种就惯性去打赌的概率赌博。它使看清那未预见的事物更加困难。它将增加“噪点”的数量,就像它将增加随意的阐释那样。
更不用提那些干扰你手机拍摄的外界因素。各种系统都可以远程开启或关闭你的手机相机,比如公司、政府、军队。你的手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能被禁用,例如在抗议游行附近录制功能被封锁,或者反过来播送它即时看到的画面。同样地,一台设备可能会被编程,从而自动像素化,清除,或封锁秘密、版权、色情内容。
它可能装配一个所谓的“阴茎算法”,以筛选出不适合工作的/不安全的(NSFW- Not Suitable/ Safe For Work)内容,它将自动修饰阴毛,拉伸或删除尸体照片,交换或拼贴上下文,或插入有地域针对性的广告,弹出窗口或实时供稿。它可能会把你或你社交网中的某个人举报给警察,PR机构或网络诈骗人。它可能会标记你的债务,玩你的游戏,播报你的心跳。运算摄影已经扩展到涵盖上述所有的内容。
它关联着控制机器人(control robotics),对象识别(object recognition)和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技术。因此,如果你用智能手机拍了张照,这张照片更多是被预先调节,而非预先谋绘了。照片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你没料到的东西,那是因为它已经交叉引用了许多不同的数据库:交通控制,医疗数据,亦敌亦友的Facebook图片库,信用卡数据,地图,以及其他任何它想要的内容。
©NVDIA-research
iPhone11发布会介绍图像信号处理器和神经网络引擎©Google Search■ 关系摄影(Relational Photography)
因此,运算摄影先天地具有政治性,不是内容上而是形式上的。它不仅是关系的(relational),而且是真正的社会性的,无数系统和人们甚至在图片出现之前就对其进行潜在的干预。当然,这个网络系统并非中立。它的规则和规范被硬连线到其平台中,它们代表了法律、道德、美学、技术、商业以及直接被隐藏的参数和效果的混合。你最终可能会在自己的图片中被喷枪涂抹,被通缉,重定向,征税,删除,重塑,或替换。
相比于它的记录功能,相机更像是社会投射仪。它投射出一种叠加——它认为你可能想成为的样子,加上他人认为你应该购买和成为的样子。但是科技很少自主行动。人们在编程技术时,往往有着相互矛盾的目的,并受着各种实体的影响,而政治则定义了如何把“噪音”「译者注:noise在前文的图像领域中翻译为噪点,此处译作噪音」从信息中分离。
那么有哪些政策定义了这种分离呢?或者说,有什么政策首先定义了什么是噪音和信息?是谁或者什么东西决定相机将“看到”什么?这又是如何做到的?通过什么手段?甚至,为什么这很重要?
■ ■ 阴茎问题
我们来看下这个例子:在脸和屁股之间,或在“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身体部位之间划清界限。Facebook之所以叫脸书(Facebook)而不是屁股书(Buttbook)绝非偶然,因为你在Facebook上不能有任何屁股(照片)。但它是如何清除掉这些屁股的呢?
一位愤怒的自由工作者向我们泄露出一份清单,详尽地说明了Facebook是如何搭建维护它的脸面,并向我们展示了众所周知的事实:裸体和性爱内容被严格禁止,除了对艺术裸体和男性乳头,而此政策对暴力内容大为宽松,甚至斩首和大量流血画面也是可接受的。
清单中的一条方针显示:只要看不到内脏,被击碎的头部和四肢可以接受;深度伤口可被展示;大量血液可被展示。这些规则仍被人为执行着,更精确地说,是被来自土耳其,菲律宾,摩洛哥,墨西哥和印度的国际外包劳工完成,他们在家工作,每小时挣四美金。这些雇工要对可接受的身体部位和不可接受的身体部位进行辨认和区分。
原则上来说,对公开发表的图像制定规则并没什么错。在线上平台实施某些过滤程序是有必要的:没有人想收到报复性的色情与暴力内容,无论这类图像有没有市场。问题的关键是在何处、如何划此界线,以及谁代表谁去划。谁决定了信号与噪音?
让我们回到消灭色情内容的问题。有针对它算法吗?就像脸部识别那样。这个问题首先被所谓的“Chatroulette难题”公开提出。Chatroulette是一个俄罗斯的在线视频服务,人们可随机视频聊天。它很快以它的“下一位”按钮而出名,相比之下“取消赞的按钮”会客气得多。 该网站的用户在2010年首先激增至每月160万用户。
但随后出现了所谓的“阴茎问题”,指的是很多用户开始在此网站上裸聊。一个网络竞赛的获胜者呼吁解决这个问题,他巧妙地建议对视频源进行快速的面部识别或眼睛跟踪扫描——如果无法辨认出任何面孔,则推断这是阴茎。
英国特勤局也采取了一模一样的工作流程,他们使用的密探程序Optical Nerve秘密地批量摄取网民的摄像头。 为了开发脸部和虹膜识别技术,他们截获了180万雅虎用户的视频源。但是,毫不意外,大约有7%的视频根本就没有出现脸部。所以,和Chatroulette的例子一样,他们对所有事物进行面部识别扫描,尝试去排除那些不是脸部的内容,定性其为隐私部位。但效果不佳,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在一份泄露的文件中承认失败:“我们还没有完备的能力去审查违规材料。”
©towards data science
随后的解决方案变得稍有复杂。概率色情检测通过计算图片中某些区域的肤色像素的数量,来产生复杂的分类公式。 但是这种方法很快就被人们奚落,因为它产生了许多误报,例如错误识别带包装的肉丸,坦克或机枪。 而最近的色情检测应用程序则使用了自学技术(self-learning technology),这种技术基于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s),计算动词理论(computational verb theory)和认知计算(cognitive computation)。 他们不是从统计学上去猜测图像,而是通过从物体之间的关系中去识别物体的方式来理解图像。
根据开发者Tao Yang的描述,认知视觉研究有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它基于对认知的量化,使其可测量和可计算。 尽管仍然存在相当多的技术难题,但这个研究方向代表了规范化(formalization)的新水准,代表了图像的新秩序和语法,代表了一个针对性行为、监视、生产和信誉的算法系统,这个系统与公司和政府的社会关系的语法化(grammatization)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是如何运作的呢?Yang的色情检测系统必须通过大量浏览不合规矩的内容来学习辨认和推断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基本上你需要在电脑里首先载入大量你想要消灭的照片类型。各种身体部位的照片文件夹形成了这样一个资料库,等待你输入它们之间的正式关系。这些文件夹的名称不仅有「阴道」,「乳头」,「肛门」,「口交」,还有「肛门/只有肛门」,「肛门/连带阴道」。在这个资料库的基础上,各种各样的检测器准备就绪:胸部检测器,阴部检测器,阴毛检测器,舔阴检测器,口交检测器,肛门检测器,手摸阴部检测器。
这种语法以及部分物体资料库让人想起罗兰·巴特的“色情语法”概念,他在其中将萨德的作品描述为一个身体部位和姿势的系统,可以随时变换每种可能的组合。 然而,这个被边缘化和公开迫害的系统可以看作是对在所谓的启蒙运动中展开的更普遍的知识语法的反映。
裸体检测系统©e-flux
米歇尔·福柯,西奥多·阿多诺以及麦克斯·霍克海默将萨德的性爱系统和主流分类系统进行比较。两者都通过计算,检索,创造竭尽的、学究的和繁琐的分类来阐明自己。Yang先生热衷于将身体部位和彼此间的关系形式化,这同样反映出人们致力于将认知,图像和行为变得越来越可量化,并且和基于数据的交换价值体系相称。
因此,那些不合时宜的身体部位变成一个新的可机读的,基于图像的语法要素。信誉和控制网络通常与此语法平行操作,但也可以随时与之链接。它的结构可能是对某种当代模式的一种反映,这种当代模式对基于数据的“知识”进行收割,汇总并将其金融化。而这些“知识”则是被嵌入到科技中的嘈杂而片面的社会算法所大量炮制出的。
■ ■ ■ 噪音与信息
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那些把噪音从信息中清除出去的社会政治算法究竟是什么?再一次,我们强调在政治上,并非算法上。雅克·朗西埃已漂亮地指出此种“清除”回应的是一个更古老的社会公式:分辨噪音和言论是为了将群众分成公民和下等民。如果有人不想把另一些人严肃对待,或者想限制他们的权利和地位,那么此人只要假装他们的言论不过是噪音,无病呻吟或无理取闹,因此把他们从主体中剔除,更谈不上权利的持有者了。
换句话说,这种政治栖息在一种有意识的解码行为之上——把“噪音”从“信息”中分离,“言论”从“呻吟”中分离,“脸部”从“屁股”中分离,然后将其结果整洁地堆叠到垂直社会阶级中。智能手机相机目前所使用的算法科技在照片出现之前就去定义照片也是类似行为。
从朗西埃的观点出发,我们或许还要处理一个更传统的想法——政治作为代表(representation)。如果每个人都听起来或看起来被代表了,没有人被降格为噪音,那么平权将会离我们更近一步。但是网络更迭得如此剧烈,以至于代表政治的几乎每个参量都发生转变。目前为止,越发多的人可以上传几乎不限数量的“自我代表”(自拍)。同时,议会民主的政治参与度似乎又在减少。当图片海量涌动,精英却在收缩和集中权力。
更重要的是,你的脸不仅和屁股,还和你的声音和身体断开联系。你的脸现在是一个元素——「脸部/脸部和手机」,预备着与资料库中的其他任何元素组合。如果有需要,还会给你的脸添加标题或纹理。图片更多地作为一种代理(proxy),表象的雇佣兵(mercenary of appearance),而非实物的代表。人被剪辑、混合、组装、合成。
人和物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星座中交缠在一起,成为网络机器人(bots)或赛博格(cyborgs)。当人类将情感,思想和社会性注入算法,算法会反注入进我们所谓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这种转变现已嫁接给漂泊在信息空间的后代表性政治(post-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
■ ■ ■ ■ 代理军队
让我们看一个后代表性政治的例子:推特上的政治机器号大军。推特机器账号是能模仿人类社交媒体活动的脚本。在大量同步的数据里,他们已经形成强大的政治军队。推特聊天机器人是一个戴着人脸面具的算法,一个动态的诈骗公式。这是用来模拟认为操作的脚本。
机器号大军通过对推特的标签(hashtag)投放垃圾广告,游客照片或随便什么内容,来影响推特上的讨论。他们做的基本上就是添加噪音。机器号大军活跃在墨西哥,叙利亚,俄罗斯和土耳其,早有传言这些国家的政党在操控它们。仅仅是AKP「译者注: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一党就被怀疑控制了18000个推特假号,这些账号用着罗比·威廉姆斯「译者注:英国歌手,其妻子为土耳其裔美籍演员」,梅根·福克斯和其他名人的照片。为了凸显真实性,这些账号不仅仅发推带AKP的标签,还会引用比如托马斯·霍布斯等哲学家,或《附注:我爱你》这样的电影。
那么,机器号大军代表了谁?(如果他们真的代表了任何人),以及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让我们研究一下AKP的机器人。罗比·威廉姆斯,梅根·福克斯和Hakan都在宣传“飞扬的塔伊普(Flappy Tayyip)”,这是一款由AKP当时的首相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如今是土耳其总统)“主演”的手机游戏。他们的目标是劫持“#土耳其推特”这个标签,来抗议首相埃尔多安对推特的封锁。同时,埃尔多安自己的推特机器号则着手绕过这个标签。
豌豆荚曾上架“Flappy Tayyip”,且有451次下载。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Hakan,这是一个由粘贴复制的脸,外加产品置入的网络机器人。通过谷歌图片搜索,只需几分钟就能把他的脸匹配到原来的身体。事实证明,在他的企业推特账号上,他在出售他的内衣,他在网上以情感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身份工作。让我们称这个版本为Murat,来给这场混战中加入另一个别名。但是哪个机器号用着Murat的脸?机器号大军又代表着谁?为什么Hakan会从那么多个哲学家中引用霍布斯?引用的哪本书?就让我们猜想是霍布斯最重要的著作利维坦。利维坦是由绝对主权国家执行的社会契约的名称,目的是为了抵御人类互相捕食的“自然状态”带来的危险。 有了利维坦,不再有民兵,也没有每个人对每个人的分子战争。
但是现在我们似乎在这样一个情况里:立足于这种社会契约的国家系统似乎在许多地方瓦解了,只剩下一组受监管的相关元数据,表情符号和被劫持的标签。一个机器号大军是当代民意,是社交网络中人民的声音。它可以是一个Facebook民兵,可以是你的低成本个性化暴民,你的电子雇佣兵或某种代理色情。想象一下你的照片为它们所用,这将是你的照片变得自治,活跃,甚至好战的时刻。
机器号大军是名人民兵,在魅力、宗派主义、色情、腐败和保守宗教意识形态之间疯狂地跳来跳去。后代表性政治是机器号大军之间的战争,是Hakan和Murat之间的战争,是脸和屁股的战争。
这也许是为什么AK党的色情明星号绝望地引用霍布斯:他们已经疲倦了以色列国防军的罗比·威廉姆斯,叙利亚电子军的罗比·威廉姆斯和革命制度党「译者注:墨西哥于1929年成立的党派」或阿姆阿德米党「译者注:Aam Aadmi Party成立于2012年,目前是印度德里的统治党」的罗比·威廉姆斯之间的战争,他们已经疲倦了为独裁者们转发垃圾营销,他们期待的是任何日托,强制管理,或支付得起的牙齿护理的实体组织,无论他们是叫利维坦还是莫比·迪克「译者注:19世纪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也叫白鲸记」甚至是飞扬的塔伊普。他们似乎在说:“我们将为你转发任何你有的社会契约!”
现在让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因为可能已经有一个模型出现在视野里。毫不意外,它还是涉及到算法。
■ ■ ■ ■ ■ 区块链
区块链统治似乎实现了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愿景。“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将会在区块链中记录和储存交易,类似于运行和验证比特币的那种。但是这些公共数字账本可以同样地对选票或法律进行编码。 以比特会议(bitcongress)为例,它正在发展一个分散的投票和立法系统。 这可能是恢复问责制和规避权力垄断的模型,但最重要的是,与技术紧密联系的社会规则应运而生,好似利维坦2.0版:当与设计它们的程序员分离时,不可信任的区块链包含被算法统治的幽灵,漂浮在人类事务之上……这本质上是互联网作为科技利维坦(techno-leviathan)的景象,一个我们可以遵循其规则的被奉若神明的加密主权。虽然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没有一个实体拥有最高掌控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在掌控。就像智能手机摄影,得由多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告诉它该如何工作。更重要的是,作为代理“人”的网络机器人将会被作为统治的网络机器人代替。
但是,我们需要再次发问,我们谈论的是什么网络机器人?谁编程了它们?它们是赛博格吗?它们有脸或屁股吗?并且,谁在规划界限?他们是社会熵和信息熵的啦啦队长吗? 是杀人机器吗? 还是一种我们已经成为其中一员的新型人类?
让我们回到最初:如何从噪音中分离出信号?运用这种分离来进行统治的古老的政治技术是如何随着算法技术一起改变的?在所有的例子中,对噪音的定义越来越多地依靠于有脚本的操作,自动化的描绘,或者决策制定。另一方面,此过程潜在地引入大量反馈,以致描绘变得相当不可预测,它比施乐打印机更像是变幻莫测的天气。 可能性(likeliness)受控于机率(likelihood)——现实只是扩展了的概率计算中的一个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代理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半自治参与者。
■ ■ ■ ■ ■ ■ 代理政治
为了更好地理解代理政治(proxy politics),我们可以从草拟下面这份清单开始:
你的相机可以自主决定照片中出现的内容吗?
当你微笑时它会关闭吗?
如果你取消下一步操作,它仍会自己启动吗?
在“金砖四国”中薪资低廉的外包IT员工是否可以管理您在社交媒体上的母乳喂养和斩首的照片?
伊丽莎白·泰勒在推特上发了你的作品吗?
是否还有其他网络机器人决定将您的作品归类为泌尿成人色情?
这些网络机器人中是否有一些忙着在转发人体孔口的图片时列举国家名称?
你的结果呈现出来是否是这样?
(*’I`*)(*’σ з`) ~♪
(*’台`*)
(*≧∀≦*)
(*゚ェ゚*)
(*ノ∀`*)
(/∇\*)。o○♡
(/ε\*) (/ε\*) (/ε\*)
恭喜你!欢迎来到代理政治的时代!
代理(proxy)是一个授权为他人去行动的代理人(agent),替代者(substitute)或一份授权给代理人的文件。但是代理现在也可以是一个有着糟糕头发的设备;一个没有被充分授权的代理人;一个因着装要求被抓个正着而进退两难的脚本;一个“说服债务人”的检测器因生殖器的像素概率「译者注:一种识别色情图像的手段」而发脾气;一架无人机耍流氓;或是聊天机器人的代表团随意将普京的专业洗发水广告投放到你的Instagram。也可以是更严肃的事情,以类似的方式破坏你的生活——抱歉了生活!
代理是负责消除噪音的设备或脚本,也是产生这种噪音的机器人大军。 它们是面具,人,替身,路由器,节点,模板或通用占位符。不可预测性是它们的通性——考虑到它们是由于概率最大化而出现的,这更加自相矛盾。但代理不仅仅是机器人或替身,代理政治也不仅仅局限于数据流。代理战争是一种相当标准化的战争模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西班牙内战。
代理给地缘政治增加了回声,掩饰,扭曲和混乱。冒充民兵的军队(或冒充军队的民兵)重新配置或直接炸毁领土,并重新分配主权。 连队伪装成郊区的特百惠俱乐部,实则是游击队和外籍兵团。 一支代理军队为了被雇佣而组成,或多或少带有意识形态的装饰。私人安全,私人军队公司,自由职业叛乱分子,武装替身分子,国家黑客和被挡在中间的人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要记住合作军队对于建立殖民帝国是异常重要的(比如东印度连队),而公司(company)这个单词就是来源于军队的一个单元。代理政治是后利维坦现实的一个主要例子。
现如今这一系列活动早已转为线上,结果显示代理战争通过不同的方式成为公共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的延续。除了市场营销工具转而服务于反暴乱行动之外,还有一系列要求更为精湛技术的政府黑客(或反黑客)活动。但并不总是这样,正如土耳其左翼黑客小组“红色黑客”所提供的信息,安卡拉「译者注:土耳其首都」警察服务器的密码是12345。
试图去阐述线上代理政治正在重新组织地缘政治就像在说汉堡企图去重组奶牛一样。的确,就像肉饼用塑料,将有机残余物和前身为纸的材料与奶牛的一些部位组合在一起,代理政治安置公司,国家,黑客分队,国际足联和凯特王妃为对等的相关实体。这些代理创建网景(netscape)来撕裂领土,而这些网景已有相当部分从地理和国家司法中断链。
但是代理政治还有另一套操作方法。一个简单初始的例子就是用代理服务器绕过当地网络审查或传播限制。当人们使用VPN或其他互联网代理以逃避网络限制或隐去IP地址时,代理政治就以另一种身份出现了。在伊朗或中国这样的国家,VPN被大量使用。但实际上,哪怕是审查制度比较宽松的国家,很多公司也在使用VPN。在土耳其,人们使用了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更改DNS到土耳其以外的数据通道,在埃尔多安短暂的推特禁令中,大家从香港和委内瑞拉发送推文。
在代理政治中,问题实际上是如何通过使用替身(或被替身使用)来行动或代表,以及如何使用中介来绕开他人的信号或噪音。 代理政治本身也可以被扭转和重新部署。代理政治堆叠了界面,节点,地形和纹理,或使它们彼此断开。 它断开身体的各个部位,并通过启动和关闭它们来创建经常令人惊讶和无法预料的组合——打个比喻,甚至是带有屁股的面孔。他们破坏脸和屁股之间看似是强制性的决定,甚至破坏两者必须属于同一身体的原则。
在代理政治的空间中,身体可以是利维坦,标签,法官,国家,植发仪器,情绪聊天机器人,或是自由职业的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通过代理和替身,身体被强加在各类身体上。但是这类组合也会对身体(和身体部位)做减法,并将他们从永无止境的界面疆域中抹去,从而进入持久的隐形。
又或者是非常简单的东西?我曾实验拿着我的手机对着推特机器号@leyzuzeelizan(现已被删除)的头像。我尽我所持有的权力,命令手机对此头像进行视网膜扫描并通过其网络数据库发送,并希望它不会反过来扫描我。我的手机不费吹灰之力就识别出了她,@leyzuzeelizan不是什么别人,正是我自己。从信号变成了噪音,从脸变成了屁股,然后又回来几次,穿越了几个国家的边界和无数高耸的栈道,消除了身体、民族、物种和媒介之间的差异 ,来宣传Hito Steyerl的作品《#口交,#xhamster「译者注:某色情网站」,#视频,#叙利亚,如何不被看到》「译者注:Hito Steyerl的原视频作品名称叫《如何不被看到》」
How Not To Be Seen, 2013
©Hito Steyerl
最后,没有屁股的脸无法坐下,它必须有一个支撑(stand)。没有脸的屁股则需要一个替身(stand-in)来完成绝大部分的交流。代理政治正是发生在用一个支撑或是用/被用一个替身之间。它处在一个替换,堆叠,掩饰和拼贴的领土,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在发生。
「原文注:Tiziana Terranova写道:“信息的文化政治极为重要地关乎着质问可信的(propable),可能的(possible)和真实的(real)之间的关系。信息的文化政治涉及对可能性结构的刺探,消除了“真实”与“已有”共同制造的巧合。”“然而,真实的和可信的之间的关系同时激发了不可能的,波动的,因而虚幻的幽灵。这样,信息的文化政治某种程度上抵抗了社会变革的限制,这种限制将社会变革封闭在一系列相互排斥和预先决策好的选择之中。同时,信息的文化政治利用虚拟的变革潜力(这是无法衡量的)来积极参与(变革)。”」
【1】本文源自2014年5月关于流通主义(circulationism)的演讲,约瑟芬·波斯玛(Josephine Bosma),梅塔芬(Metahaven),戴维·里夫(David Riff)和伊托·斯蒂尔(Hito Steyerl)之间的讨论,是由安妮·弗莱彻(Annie Fletcher)在Van Abbemuseum为斯蒂尔策划的回顾展中的一部分。后发表在e-flux第60刊,2014年12月。
【2】作者:Hito Steyerl 出生于1966年,德国。是一位影像艺术家,电影创作者和作家。她的主要兴趣在于媒介,科技和影像的全球流通。Steyerl毕业于维也纳艺术学院的哲学博士,目前在柏林艺术大学教授新媒体艺术。
【3】译者:吕芃,出生于1996年,中国。是一位影像创作者,毕业于帕森斯设计学院摄影系,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像素译文系列
我们该如何讨论当代艺术中的摄影?
人类仍是观看的主体吗?
